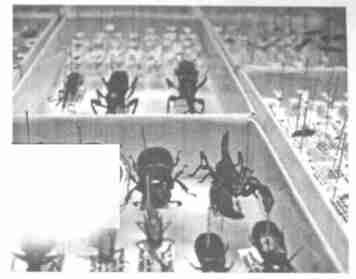
过去7年以来,美国农业部动植物卫生检查处技术援助实验室主任罗伯顿 · 斯特顿(Robert Staten)和加州大学的同事们一直在修理棉红铃虫的DNA,棉红铃虫是一种与柠檬种子大小差不多、正在毁坏整个美国西南部棉花作物的令人讨厌的昆虫。例如,加州的帝国流域曾经是10万余英亩棉花的基地,但现已大部分被棉铃虫蛀食,不到10年就使可种植面积缩小到仅仅5000英亩。科学家们的目的是培育带有致命遗传缺陷的棉铃虫,以便有效地使其不育。一旦在棉田里释放这种棉铃虫蛾,它们就会与野生群体交配,过一段时间后,该物种便会灭绝。
加州棉花病虫害防治局局长沃利斯 · 施罗普希尔(Wallace Shorpshire)说:“你需要防治这些小害虫的武器。我认为用遗传学方法改良棉红铃虫可提供一线希望。”
人类已经设法征服了大部分物质世界,现在,虽然遗传改良作物的价值争论仍在进行,但科学家们已开始把这种技术应用于昆虫。斯特顿的计划只是其中一例。欧洲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遗传学方法改造蚊子,使其不能传播疟疾。同样,亚特兰大疾病防治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在研究传播南美锥虫病(一种潜在的致命热带病)的甲虫。尽管这种方法的潜在利益是巨大的,但许多环境保护论者警告说其弊端可能是灾难性的。
美国农业部不想轻率地冒那些风险。在释放遗传不育棉铃虫之前,斯特顿对棉红铃虫的基因作了调整,使这些虫蛾不再携带终止基因,而拥有一种无害的跟踪基因。今年晚些时候,斯特顿希望把大约2300只这样的棉铃虫蛾放入棉田上撑起的封闭帐篷里,以便研究它们的行为。
自1970年起,斯特顿就开始对灭棉红铃虫的研究。由于这种害虫的神秘生命周期,即使效果最显著的农药也不能对它起到灭杀的作用。棉红铃虫大部分的生活是深藏不露的,幼虫在棉铃的深处营巢,或躲藏在土壤的缝隙里。这种昆虫只度过一周左右的成虫生活,而且只在夜间出现。
减少棉红铃虫群体的另一种方法是用大剂量辐射使一些雄虫绝育。但这种技术会严重损害雄虫,以致它们几乎不能再与野生雌虫配对。斯特顿说:“经历过化学疗法的人都知道辐射导致衰弱。”
科学家们也尝试过一种更间接的方法:设计一种能自己产生杀虫剂的棉花作物,以此来灭杀吃这种植物的昆虫。但值得担心的是,久而久之昆虫可能对这种作物产生抗性,政府官员已限制种植这种改良的棉花。
大约在10年以前,斯特顿偶然发现了另一种选择。他在一次宴会时的谈话中,获悉他的一位同事成功地把一种果蝇的基因与另一种果蝇的基因进行了交换。他能得到符合需要的果蝇基因、并把这种基因转入棉红铃虫吗?斯特顿取得了加州大学昆虫学教授汤姆 · 米勒(Tom Miller)的帮助,开始了这项研究。
最有吸引力的选择是向棉铃虫提供使虫卵不能成熟的终止基因——牛津大学遗传学家卢克 · 阿尔菲(Luke Alphey)发现的基因。但必须首先解决怎样使这种基因进入害虫的问题。他们决定把这种基因附在一片叫做转位因子的DNA(或称跳跃基因)的背上,跳跃基因是一种具有把自己插入染色体的特殊能力的基因序列。然后他们把携带终止基因的跳跃基因注入虫卵,以求这种结构物能“跃入”棉红铃虫的DNA中。
但有一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既然终止基因阻止虫卵发育,那么斯特顿和米勒怎样才能使遗传改良的棉红铃虫在实验室里发育呢?他们需要为终止基因提供一个切断开关。
在研究中,阿尔菲发现了利用一种对普通抗菌素——四环素起反应的特殊基因作通断开关的方法。一旦把这种基因连在终止基因上,斯特顿和米勒只要给棉红铃虫添加微量四环素,就能解决这一问题。
然而,环境保护主义者担心,采用上述方法把棉红铃虫逐出食物链,可能使当地的生态系统失控。如果提供新的转基因昆虫,他们担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会缺乏监视这些程序的技能。
对此,斯特顿认为,棉红铃虫不是美国的土生昆虫,消灭它们不会破坏现有的生态系统。以这种棉铃虫为食物的蝙蝠和其它食肉动物是泛食者,有大量其它昆虫可供食用。
然而,更严重的威胁是跳跃基因可能具有足够的能力径直跃入另一个物种,——使其灭绝。一些批评家指出,遗传工程玉米的基因已经跃入常规作物中,他们担心相似的跃跃可能在棉红铃虫和别的昆虫之间发生。
阿尔菲反驳说,即使发生这种转移,这种特性也不会扩散。因为这种基因会破坏虫卵发育,所以接受这种基因的任何生物都不能生殖。
但实验室的结果并不总能按原样重现在田间。没有人比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昆虫学家马乔里 · 霍伊(Marjorie Hoy)在几年以前就进行的遗传改良螨的试验。霍伊在实验室发现这种添加基因几乎能正常工作200代。但一旦把这种螨放在野外试验,其基因就失效了。
格林皮斯公司遗传工程科学顾问多林 · 斯特宾斯基(Doreen Stabinsky)说:“这是一个关乎你能容忍多少风险的政治决定。把遗传改良牛放入环境中是一回事;释放无法控制或无法召回的遗传工程昆虫又是一回事。”
有人带着希望和担心的口气问斯特顿:“你一定能做好这事吗?”
他回答说:“这是高报偿、高风险的冒险事业,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但从长远来看,它对社会的回报无疑是大有潜力的。”
[Popular Science,200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