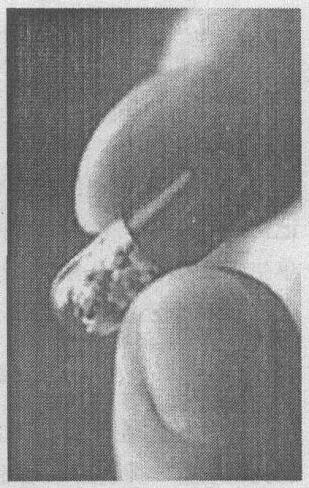
在新泽西州北部的一个实验室,研究人员在分子水平上探索着错综复杂的记忆过程,希望研制出用于大脑的“伟哥”——一种可以使处于衰退状态的器官恢复青春活力的化学药物。
长期以来,从事记忆药物的研制工作曾是科幻题材,目前生物制药公司在这场设计可真正有效增加记忆的药物的科学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新一代的药物能改进因患疾病或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记忆力减退。
“当这种红色的小药丸刚一出现,我的朋友们就不断打听,"埃里克 · 坎德尔(Eric Kandel)说。这位现年73岁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也是这一研究领域的领袖人物。1998年他的记忆药物的研制工作还毫无进展,但是在2000年则与他人分享了诺贝尔医学奖。“如果我们能像现在一样继续取得进展,我们将在5~10年后得到可以治疗因年龄增长造成的记忆衰减的药物,'他说。
在这场研制记忆药物的竞赛中,现年48岁的蒂莫西 · 塔利(Timothy Tully)是坎德尔的有力竞争者,蒂莫西是纽约冷泉港实验室的研究员,也是赫利肯疗法的创立者,目前正在研究世界药剂市场中的下一个热点——改进和提高记忆的药物。
回 顾
增强记忆药物的第一批使用者将是美国400万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同时,记忆药物也可帮助其他数百万有轻微认知障碍、头部外伤、并发症或心智发育迟滞,以及在严重的中风后处于痊愈阶段的病人。一些新的药品甚至可以摒弃不再需要的记忆。
很吸引人的一点是:这种药物可能会受到5000万美国中年人的欢迎——需要用它来改变因年龄增长而产生的健忘现象。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神经科学专家詹姆士 · 麦高夫(James McGaugh)说:“药物公司不会告诉你的是,他们在帮助患者改进记忆的同时,还瞄准了一个被禁止的市场定位——那些试图记住客户名字的中年推销员群体。”
但是,如果这种药丸流行起来,上百万的健康人寻求智力优势的努力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危机。一种作用过分强烈的药物可能会导致情感上的失控,或者会导致大脑被大量杂乱无章的记忆所充斥。在这种药丸被用于改善那些轻微的缺陷之前,必须被证实不会产生任何严重的副作用。药物的使用者很可能不清楚一种会改变生活方式的药物所带来的那些相关的风险。
低等生物
当然,这些药物是否将会符合我们的期望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坎德尔和塔利成功,他们将永远地改变医学以及我们将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莱恩 · 笛卡儿将整个世界区分为“外延”(物质世界)和“思想”(精神世界)——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哲学家和科学家一直在辩论人的思想是否真的那么难以捉摸,永不可知。塔利说:“笛卡儿是错误的。记忆是一个生物学过程,它就像别的事物一样也能被操纵。你不仅能使之消失,你也能改善它。”如果有一天,一瓶记忆药丸真的出现在你的床头,无数的赞誉将归于塔利和坎德尔,还有两种低等生物:果蝇和海蛤蝓。
坎德尔目前之所以会在这场竞赛中担当这样的角色,可以一直追溯到1929年的维也纳——他在孩童时期产生的心理体验。坎德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来到美国的,关于纳粹的恐怖记忆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中,这也是驱使他对记忆进行研究的部分原因。作为一个年轻、前途远大的精神病学家,坎德尔孤注一掷地将他的事业都押在一个预感上——通过研究海蛤蝓来了解人类的记忆。几十年以来,他的实验室在这一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
塔利的履历则一目了然。他是出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市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乌尔班纳平原上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从事遗传学研究。经过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实验,他的研究小组已经培育出了带有精确持久记忆的果蝇。
坎德尔和塔利的研究结论令人吃惊:人类基本的记忆构造机制可能与那些海蛤蝓、果蝇以及其他的简单生物相似。所有动物的脑细胞似乎都很类似;不同之处只在于连结脑细胞的复杂度。
遗忘作用
当坎德尔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有关记忆的研究时,这一领域的一切都还很不明朗。科学家们假定人类记忆的机制与那些低等生物有着极大的差异。
原本打算成为心理分析学家的坎德尔在进行了令人着迷的神经生物学研究之后转入对记忆的研究。他之所以介入神经生物学领域是想借此研究人类的行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科学家们获得第一个重要的线索:记忆是如何形成以及是在哪里形成的?一个27岁的患者,我们只知道他名字的首字母是H. M.,有严重的癫痫症。为了治愈他的疾病,医生们切除了他大脑中的海马体——位于大脑中央的一个小凸起。这个病人的癫痫症差不多好了,并且也能正常思考了——但是不能回忆起几秒钟以前的事。奇怪的是,H. M. 仍然可以毫不困难地回忆起他的孩童时期。这表明海马体是将即刻的知觉转换为记忆的重要器官,然而却不是记忆存储的场所。
坎德尔专注于对记忆过程背后的脑细胞工作方式的研究。他选择了海蛤蝓,因为这种生物研究起来比较容易:它有20000个神经细胞,甚至不用显微镜就能看到(人类则有超过1000亿个神经细胞)。通过一系列划时代的研究,坎德尔展示了海蛤蝓是如何由基本的条件反射形成简单记忆的:当它受到威胁时,是如何闭合它们的鳃。他掌握了操纵蛤蝓神经细胞中的化学过程的技术(而这也暗示,人类的脑细胞也可被操纵),他能够增强蛤蝓的记忆力。
通过被访问的神经键间的空隙,脑细胞释放出一些化学物质以进行彼此间的联络。通过暂时性地强化相关的脑细胞间连接,大脑可以创建一个短期记忆。这种记忆会在几分钟或几小时后逐渐消失。通过使用新蛋白质加固连结脑细胞的神经键,可以将长期记忆固定于大脑某处长达几周或几年。想象一下,对只需使用一次的电话号码,你把它查出来之后就记在脑子里了,而在几分钟之内,你就会忘掉它。但是对你需要反复使用的号码,你要经常复诵它以便将其留在你的记忆里。不过,毫无疑问即便是长期记忆也会受到时间的侵蚀。
聪明的果蝇
分子生物学在上世纪70年代取得的进展使坎德尔和其他研究人员能在分子层次上探究记忆的奥秘。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些分子的运转,那么就会更容易地找到药物作用的靶点。
坎德尔揭示了一类信使分子——被称为环腺苷酸的分子——在记忆形成中扮演了一个中心角色。它存在于细胞内,当接收到神经细胞发出的信号后,就立即打开开关,激活某些特定蛋白质。这种蛋白质被激活后,可以在两个神经细胞之间暂时地起到提高连结强度的作用(想象一个在接力赛中交接接力棒的赛跑者)。但是环腺苷酸只是一个信使;它并未参与建立长期记忆所需的蛋白质的制造过程。
1990年,坎德尔发现了一种有趣的分子,称为CREB。这种分子对于学习和记忆是非常重要的。他的研究小组能够展示,如果在蛤蝓的神经细胞中阻断GREB,也就同时阻断了创建新的长期记忆的过程。
在理解CREB是如何影响记忆的问题上,大多数引人注目的证据出自蒂莫西 · 塔利和他的同事杰瑞 · 因的研究成果。塔利使用的果蝇比海蛤蝓有更多的优势:更为广泛的生存习性,更易于进行遗传工程改造并且能够在试管中数以百万地进行培育。1994年,塔利和杰瑞通过基因工程培育出了携带有持久准确记忆的果蝇,这些果蝇的CREB蛋白质都处于“开启”位置。
普通果蝇用了十次训练学会了不进入那间有异味的房间(如果它们进入房间就会被电击)。但塔利的超级果蝇只需学习一次就够了。自那时起,其他一些研究者已经证实CREB在老鼠身上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万事俱备?
海蛤蝓和果蝇的试验证明,CREB有助于产生在神经细胞之间建立永久连结所需的新蛋白质。正是在这些连结中,长期记忆得到了存储。同时,塔利和坎德尔的研究小组也发现了第二个因素:CREB抑制物。杰瑞和塔利利用遗传工程培育出了带有过多CREB抑制物的果蝇,这些果蝇甚至在许多次尝试之后也没能形成记忆。
环腺苷酸和CREB是记忆药物开发的目标。与此同时,塔利和坎德尔还在寻找其他会影响记忆的基因和蛋白质。
塔利认为,成功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取得成功,”问题在于到底在何时可以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