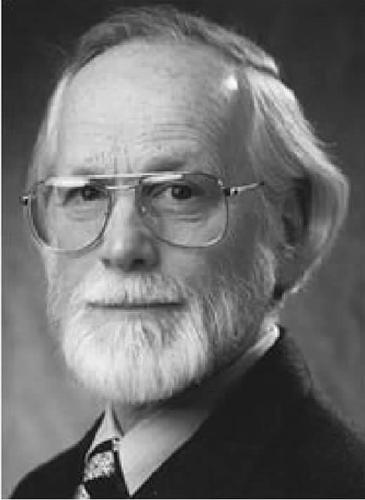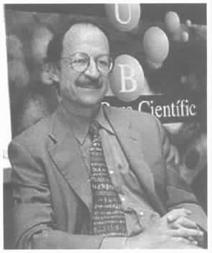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毕晓普接受诺贝尔基金会网站访问,畅谈——
为配合今年诺贝尔奖的颁布,诺贝尔基金会网站发布了由该网站记者对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迈克尔·毕晓普(Michael Bishop)博士的视频访谈资料,所谈内容涉及科学家如何做出创造性工作,以及科学和艺术、宗教间的内在联系等,为使读者了解科学大师的亲身感受,本刊特刊出该次访谈内容。
记者:欢迎访问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1989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毕晓普(Michael Bishop)博士。毕晓普博士因发现了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的细胞起源而与哈罗德·瓦姆斯(Harold Varmus)一起分享了该项殊荣。他的工作非常有趣,同时他也写了一本关于他的科学生涯的很有意思的书,书名是《怎样获得诺贝尔奖》。毕晓普博士,您不会是认真的吧?毕晓普:哦,当然不是。这个书名是带有自嘲意味的。它原本是我的一个讲座的标题,结果听众们觉得十分有趣,于是我决定就用它作书名了。我的一些朋友们反对我用这个书名,他们觉得这样给人的感觉很傲慢;另一些朋友却支持这个书名,他们理解我的用意,知道我是用它来自嘲的。所以想要获得诺贝尔奖并没有所谓的套路,重要的是“运气”,是你在合适的时间到达了合适的位置,并且时刻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位置。
记者:但是您在书中多次提到“幸运只降临到有准备的头脑”……
毕晓普:嗯,这只是我刚才的观点的一种比较正式的说法。你需要在合适的时间到达合适的位置,同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充分利用你的机会。为了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你必须要勤奋,要有充足的准备和苦干的精神。没有人可以不劳而获的。
记者:您刚才似乎忘了提“直觉”。
毕晓普:嗯,直觉与科学的关联已经无法再强调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合适的时间”达到“合适的位置”,是因为他已经深谙某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并且清楚地知道哪些是有价值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在机会到来之时,他已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潜意识里的准备。我想人们过分强调直觉这一点可能是为了让公众感到一种心理慰藉:他们可能会认为只要主观上愿意,人人都有可能在科学上取得成就。但事实是,仅仅主观的愿望是不够的,科学少不了踏踏实实的苦干。
记者:我们知道您在音乐上也有一定造诣。您能否谈一谈科学与艺术这两种创造性工作的区别?
毕晓普:嗯……音乐家也分很多种类。首先一个演奏家必须具备演奏技巧,如果他够幸运的话可能还具备对音乐的感悟能力,知道怎样去表现不同的音乐。而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他不仅要具备技巧,还需要更多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我只是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发表这些看法——我曾经尝试过成为一个杰出的音乐家,但不幸失败了。所以我认为作曲家或是画家和雕塑家的角色与科学家更为接近,他们都强调个人的洞察力、想象力和不断尝试的精神。因此,即便你已经在合适的时间到达了合适的位置,你仍然需要不断尝试才能做出重要的贡献。只有通过不断尝试才能突破旧的规律。据我所知,科学上里程碑式的进步大多与旧规律的突破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科学与其他领域的创造性工作是有关联的。我想科学与艺术的区别在于,科学要求人们具备一个相对更为庞大和系统性的知识体系。
记者:所以您认为科学与艺术的关联在于打破旧的规律?
毕晓普:是的,我认为这是所有创造性工作之间的一座基本的桥梁。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所有规律都被打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哲学化的问题。显然,在科学上我们从来没有打破过所有的规律——我们甚至连规律本身都没能全部掌握。我们可以把规律定义为当前对事物的理解,之所以有必要去打破这些规律是因为它们并不是完全正确的。“打破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其实是指对于现有常规的突破。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正越来越接近科学上的真理,因而到那时科学家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艺术方面,诸如莎士比亚戏剧之类的不朽之作仍将流芳百世……
毕晓普:我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个人的特殊重要性。如果没有莎士比亚,我相信人类的文学仍然是丰富和广博的;同样,如果没有爱因斯坦,我相信我们对物理学的认识也未必会比现在落后。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不可或缺”的,因为人类是一个如此庞大和丰富的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任何个人成就的贬低。第一个发现规律的人当然值得尊敬和崇拜。
记者:您在书中引用了诗人华兹华斯的话,是不是可以把它翻译成“诗人在写诗之前必须懂得科学,必须认识这个世界”?
毕晓普:华兹华斯是一位以关注科学对人性的影响而出名的诗人。一方面,他认为科学家对世界的认知必须建立在破坏事物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推崇科学,称之为诗歌的源泉。我的理解是:当人类发现新的规律时他也发现了美,于是他就借诗歌去歌颂和表达这种美。华兹华斯对于科学和技术的这种矛盾的看法与一个世纪后人们普遍的看法不谋而合。我想,即便是科学家也在担心着技术对于人类文化的冲击。比如全球气候变暖、物种濒危等等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由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在我看来,华兹华斯的这种担忧也主要是针对技术的发展,因为他在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科学(非技术)的洞察力的崇拜。
记者:那华兹华斯的这句话反过来说正确吗?科学家在做科学之前是否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
毕晓普:我认为对于科学家来说,其他领域的知识,比如哲学和美学等是十分重要的。这些知识使得科学家们能够认识到他们对人类社会有着怎样的影响和贡献,从广义上说,也使得他们成为更好的公民。
虽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这些知识,他们依然能够取得在科学上的建树——事实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科学家。但我想指出的是,那些最为人们崇敬的科学家都是有着丰富文化底蕴的。他们有着广泛的兴趣,往往在文化艺术方面有所涉猎,也因此本能地关注人性和人类的生存状况这些基本问题。
记者:“美学”这个词频频出现在科学领域,人们往往从美学角度去衡量一个观点或是一个方程式。那么科学发现的过程是否也与美学有关呢?比如你会倾向于选择一个更符合审美标准的理论吗?
毕晓普:这是一个语义学或者哲学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算是一个持异端者。我无法将科学和艺术这两者的美学体验等同起来。就我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科学发现来说,是的,当我们第一次认识到那个发现时的确很兴奋。但这种兴奋和我在听交响乐时感到的兴奋一样吗?不,完全不同。可能有些人在看到一个数学公式时的确能感受到同样的兴奋——这可不是我的经历,我和大多数生物学家一样,基本是“数学盲”。但也许对于数学家来说,他们看到一个精妙的数学问题时可能会感受到和听交响乐时一样的激动。我认为把这两种美学体验等同起来还是有点不妥。科学发现的美往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如开始时那么激动人心了。就拿DNA双螺旋来说吧。虽然我们都很敬仰这项工作并且深知其重要性,但现在已经无法体会到人们刚发现它时的激动之情了。而我每年去听交响音乐会时都会产生相同的兴奋感。
记者:您在书中也提到您对教学和科普写作有着很大的热情……
毕晓普:嗯,教育在文化中占有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教育和传播,文化就会消亡。传授知识似乎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往往会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快乐。比如像我就很乐意为公众解释癌症的一些机理,消除人们的疑惑。同时这种知识的传授也宣扬了人类的洞察力和认识水平的进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美好的体验。
记者:那如果公众无法理解您所说的呢?
毕晓普: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即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对当今的科技也是知之甚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表现出很强的求知欲。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科学教育体制的不完善。可以说大学本科之前,对于非科学专业甚至包括本科阶段的科学教育都是非实质性的,完全与当今的科学发展脱节了。
图为1989 年与毕晓普同时获奖的哈罗德·瓦姆斯
记者:那其后果会是什么?
毕晓普:后果是大众对于科学的无知。他们往往对于技术的进步感到恐惧,担心人类最终无法控制技术,对于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缺乏判断力,无所适从,或者盲目迷信等等。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不相信进化论,这个结果真是令人惊讶!这就好像不相信地球是圆的……
记者:问题是我们怎么能肯定我们掌握的知识是对的呢?科学史充斥着推翻和建立……
毕晓普:这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最简单的衡量标准是看这个理论是否符合实际。比如我们在太空拍摄的照片已经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但这种证明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往往受到时代的牵连和限制。今天我们对于癌症的了解是100年前人们无法想象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关于癌症的理论可以说已经基本确立。那么它是否符合实际呢?显然是符合的。我们已经开始运用已掌握的理论开发新的疗法,应该说我们的理论已经处在了权威知识的边缘。科学家们总能知道什么时候他的理论跨越了权威知识的边界——比如当同行们的争议越来越少时。
记者:您也提到在科研过程中经常会有模棱两可的情况,用两种不同的理论都能解释同一个现象。这种情况在政治领域也很多见吧……
毕晓普:是的。正因为如此,科学家才必须做到对公众和政府部门绝对诚实。我想美国科学教育的不足可能就与此有关。我曾在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美国公众在科学上的最大盲区在于统计学知识的缺乏,因此美国人很不善于处理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他们往往喜欢非此即彼的情况,但是这样的现象现实中少之又少。多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向政府和公众宣传吸烟的危害,但这些确凿的研究结果却通常受到不应有的忽视。所以,我认为科学家们一定要诚实,尽管我们很不情愿去承认化学环境对癌症的直接诱发作用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就是事实。
记者:似乎越来越多的政治焦点开始跟科学有关了,比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以及食品短缺等等。在这些问题上,正如您所说的,目前的科学理论还并没有“跨越权威知识的边界”,您认为政治家们在这些问题上会怎样利用科学的不足呢?
毕晓普:嗯,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把那些有着政治影响的问题转化成为简单的无可非议的问题。就拿全球变暖问题来说吧——因为这和我研究的领域相去甚远,所以我现在是以一个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科学家的身份发表我的观点——目前并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地球正在逐渐变暖,虽然到过北极的极少数人可能亲眼见过那里冰山融化的场景,但这究竟是人为造成的、还是地球长期演化过程的自然趋势?我们现在先把问题搁在那儿,等几年后出了结果再说。但是,当臭氧层空洞问题已被确认的时候,我作为一个生物学家清楚地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意味着我们正在受到以前人类不会受到的太空物质的侵害,并且重要的是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这个问题是人类自己造成的。因此现在我们可以暂且撇开全球变暖问题,而把精力投入到怎样解决臭氧层空洞上。
记者:现在让我们回到您的研究领域。达尔文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但他从未提到过生命是怎样形成的。您认为这是科学永远无法跨越的极限吗?
毕晓普:嗯……谁知道呢?对我来说,在公众面前谈论科学的一个最根本原则是科学家不该对未来做任何猜测。历史已经充斥了科学家的错误预测,即便是伟大的科学家也做过错误预测。因此,我不反对开玩笑式的预测,但是我们不应该在公众可能信以为真的场合下做任何的预测。因为科学充满了不可测因素,事实上科学发展的精髓就在于其不可预测性。所以我的回答只能是“我不知道”。
记者:那这样说吧,假如有一天生命起源的谜底最终被揭开,那么华兹华斯所表达的生命的美感会不会随之消失呢?
毕晓普:如果我们找到了证明起源的合理解释,那么这个理论本身的卓越性将使他创造出更优美的诗篇——据我所知,他也并不信仰当时关于生命起源的迷信说法。
记者:那么理性的知识是否最终将使人类抛弃宗教信仰?
毕晓普:为什么人类要抛弃宗教信仰呢?我不认为这两者(科学和宗教)是相互排斥的。有些科学家的确希望看到理性的科学知识最终导致宗教体系的瓦解,但我并不这么希望。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自己是个信徒,而是我通过一些个人的经验体会到宗教信仰的确能够满足人类的某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