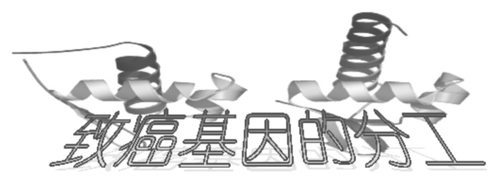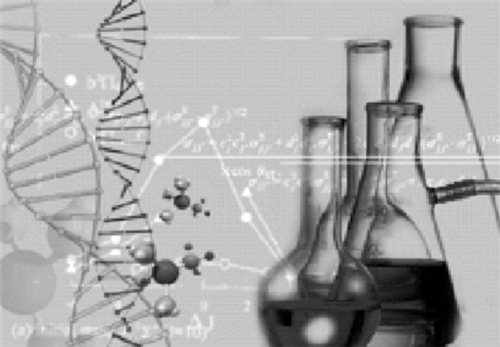有些基因与肿瘤的发展有关,其他基因则专一地促使癌细胞扩散到其他器官。一整套4个基因似乎对完成这两个过程都是必要的——
癌症致死大都由于癌转移,或癌细胞的扩散,这与某些成套基因或“标志”基因的表达与普遍的和特定器官的癌转移相关,促使临床上首次实施了筛选计划。在鉴定数量不断增多的涉及癌转移某些过程的基因的同时,寻找分子靶标以便调整治疗方法,已成为癌症研究的一个主要焦点。从事癌症研究的格普特(Gupta)研究小组不久前在《自然》杂志上报导称:4种肺癌转移标志基因促成了“多功能的血管改造计划”。
格普特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以前曾培育过乳腺癌细胞系MDA-MB-231的变异体,这些变异体显示可向骨骼或者肺进行特定器官的癌转移。通过分析基因表达图谱,他们鉴定了骨骼和肺癌转移的特定标志,并证实了某些这类基因在特定器官癌转移中的作用。格普特研究小组现已在进行肿瘤细胞中涉及这些基因功能的遗传学和药理学调控方法的实验。报道称,4种基因不仅促进主要肿瘤的生长,而且还促使癌细胞进入脉管系统在肺内繁殖,并通过血管渗透,使癌转移发展。
这4种基因的产物———表皮调节素(epiregulin),2种金属蛋白酶(two metalloproteinases)和环氧合酶-2(cyclooxygenase-2),都是癌症研究人员所熟知的。表皮调节素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一个配体,对数种癌症的生长、存活和发展有重要作用。基体金属蛋白酶(MMP-1和MMP-2)参与向肿瘤提供养份的新血管的生成以及参与肿瘤细胞的迁移和入侵。环氧合酶-2促进伤口愈合和调适炎症反应,以前还认为与促使癌转称有关。
格普特及其同事们发现,当任何这些基因在正向肺部转移的乳腺癌细胞因基因调控而丧失活力时,主肿瘤生长和肺部的癌转移仅有微小的抑制。但是当这些基因一起都丧失活力时,附加效应或协同效应就十分明显,而当上述4种基因都丧失活力时,主肿瘤生长和向肺部的癌转移几乎完全消失了。虽然在4种基因丧失活力的肿瘤细胞中的分裂繁殖未受影响,但细胞凋亡(程序性的细胞死亡)增加了。此外,这类肿瘤的血管腔室变小了,渗透性更差了,这些因素有可能增加细胞凋亡并使肿瘤细胞无法进入血流和外渗入肺中。的确,具有全部4种丧失活力的基因的肿瘤细胞是被困在肺部的毛细血管内了,而在肺部血管外面的具有正常基因的肿瘤细胞则会生长成为一个“微转移”的病灶。作者证实,在迁移试验中遗传学调控无法使肿瘤细胞渗透内皮屏障——即覆盖血管边腔的细胞层。
这些资料显示:表皮调节素、环氧合酶-2和金属蛋白酶-1和金属蛋白酶-2协同作用,可通过生成一个复杂和高渗透性的血管网络,在主肿瘤内重建脉管系统。这类网络常可在攻击性恶性肿瘤中观察到。这些蛋白质在异质的肿瘤细胞内渗入血管以及在癌转移器官的内皮屏障被破坏以利肿瘤细胞外渗时,似乎都有重大作用。相反,专一影响肺癌转移的标志基因如IL13R2,SPARC和VCAM组合的消除,却不影响主肿瘤的生长。因此,在不同种类的基因之间似乎存在着分工——癌转移基因仅仅与癌转移有关,而不涉及主肿瘤的扩张;肿瘤发展基因则在上述两方面都发挥功能。
格普特研究小组也曾用药物来专一地抑制上述4种基因产物。对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一种中和抗体cetixumab和环氧合酶-2特种抑制剂celecoxib现已在临床上应用,宽频的金属蛋白酶抑制剂GM6001已投入临床前测试。对移植了MDA-MB-231细胞系的肺癌转移变异体的小鼠进行组合治疗,基本重复了基因消除研究的结果。作者观察到了主肿瘤生长被有效遏制以及肿瘤细胞的内渗、外渗和肺部的癌转移。这种治疗还使经静脉注射初始乳腺癌细胞及其衍生物的小鼠肺部癌转移受到了抑制,这种衍生物显示具有高水平的表皮调节素、环氧合酶-2和金属蛋白酶-1。中断治疗则导致被困在肺部毛细血管内的肿瘤细胞释放进入肺的实质组织中。
这些研究对癌转移过程进行了功能性的剖析,确定了涉及癌转移过程多个阶段的特定基因。基因的和药物的调控所产生的同样结果,表明药物治疗只影响肿瘤细胞内的4种癌转移基因,而不影响肿瘤细胞微观环境中的这些基因活动,诸如内皮细胞中环氧合酶-2的活动或肿瘤内渗入的发炎细胞中金属蛋白酶-1和金属蛋白酶-2的活动。
格普特研究小组的上述发现也引起了已经困惑癌症研究人员多年的一个问题。直接(通过基因)或间接(通过外因)改变基因并为癌转移所需要的种种事件是否早已在主肿瘤细胞中预先决定了,或者说某些癌细胞是否是在“微观演化”的选择过程中获得了癌转移的能力?作者认为,某些基因和外因事件影响了已存在于主肿瘤内并为癌转移的外向扩张所需要的基因,而其他这类事件则影响仅为癌转移所需要的基因。但这些基因如何按其功能被共同选择以及是否被选择目前尚不清楚。
现在有理由进一步深入研究决定重建肿瘤脉管系统及其后果的分子机制。还有哪些其他细胞类型和因素与重建过程有关?特定的器官是如何决定的?使癌细胞的目标向着肺部的化学诱导剂和附着分子是什么?据报道,是骨髓衍生的祖细胞补充到肺部为扩散的癌细胞建立了癌转移的“生态龛”。这些细胞除了具有重建血管的功能外,是否还与特定器官的癌转移有关?外渗过程中表皮调节素、环氧合酶-2以及金属蛋白酶-1和金属蛋白酶-2的组合活动是否专一针对肺部的癌转移?这种现象也呈现于其他靶标器官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还将加上长期探索的由佩奇夫(Pagef)所提出的“种子和土壤”学说的分子活动细节,该学说认为,扩散的肿瘤细胞(种子)需要在远处器官中找到适宜癌转移的微观环境。
还有一些问题涉及格普特研究小组的潜在价值。上述4种基因是否在所有类型的乳腺癌以及有可能也在其他类型的癌症中都很重要?组合治疗据作者称已证实在临床前的情况下获得成功,是否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应用于临床?
最后从技术角度看,格普特研究小组的工作标志着一个技术上的里程碑。有能力产生同时载有被抑制表达的4种基因的稳定的细胞系,并迫使这4种基因中的3种基因进行表达,以便测试基因消除的特性,这是一项引人瞩目的实验技艺。若将这一技艺推广应用,将有助于阐明癌症发展期间多种基因的组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