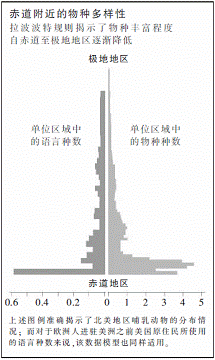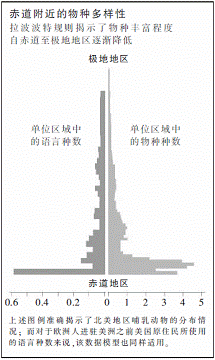如果语言的发展成就了人类的信息交流,那为何我们大多数人彼此之间压根无法言语交流?英国雷丁大学的马克·帕格尔(Mark Pagel)教授将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进行了对比,提出了有意思但很有见地的一种解释。
上帝预谋的语言壁垒?
对于那些沉迷于语言研究的人来说,巴布亚新几内亚东北海岸地区简直就是一家玲琅满目的糖果店。科拉克语居民就住在布雷姆语区的隔壁,而布雷姆语居民的对岸便是操着瓦纳姆比勒语的邻人,类似语区穿插交汇的情况比比皆是。我曾经偶遇一位来自那里的朋友,于是赶紧询问是否真的像传说中那样每隔几公里便乡音迥然。“怎么会呢,”他回答,“根本用不了几公里。”
当今世界,广泛使用的语言大概有7 000多种。也就是说,有7 000多种完全不同的表达“早上好”或是“看来要下雨了”的方式――人类作为哺乳动物的一种,所使用的语言种数比整个哺乳动物的种数还要多。更有意思的是,这7 000多种语言可能只是人类发展至今所使用过的语言种数的冰山一角。人类语言的这种多样性特征并非全然增益,比如把一只大猩猩或黑猩猩从它原来生活的群落中抓出来移置到随便一个新的群落,其与新朋友们的交流将丝毫没有障碍,驴子、蟋蟀、金鱼等等也是一样。
这就使我们注意到事关人类交流的一个有趣的悖论。如果语言的发展成就了我们的信息交流,那为何我们大多数人彼此之间压根无法言语交流?这个历久弥新的问题早在“巴别塔”的圣经旧约故事中就已经彰显无余,人类的狂妄野心足以让他们籍由共同的语言合作造成高塔直通天堂;盛怒于此的上帝毁掉了巴别塔,并加于散落各处的人们以无法互通之言语以保再无覆辙。神话将我们引向一个有趣的反讽,人类各异语言系统的存在制约了彼此之间的交流。而惊奇之处还在于,事实或许并非不是如此。
多样性与人类的群落化
语言的起源实难追溯。来源于化石的解剖学证据显示,人类祖先的言语能力成型于大约60万至160万年前之间。然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语言传达复杂观念的能力是伴随着现代人类文化性的社会活动和符号表征实践才逐渐形成的。这种确切的表达能力大约在16万年至20万年前的非洲显露雏形,直至6万年前才播徙至其他大陆板块――最终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不难想像新的语言类型会随着人们的拓疆迁徙而立告出现,因为一旦某个群落新到一处,他们的语言就会更迭革新以适应当地的生存需要。但真正头疼的问题是,最富差异性的社会构成及语言分化并非发生在迁徙活动最频繁的地区,反倒恰恰是那些人口分布密集而稳定的区域。
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相对窄小的大陆――仅仅稍大于加州――存在着800到1 000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类型,大约占全球总语言种数的百分之十五。这种语言差异性并非缘自人口迁徙亦或自然环境对人口分布的划割。恰恰相反,聚居在一起的人们仿佛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分化为迥然相异的群落社会,这种分化过于细密以致于几乎难以保证相互之间的顺畅交流。这到底是何缘由?
想到这里,我被语言性差异与生物性差异之间诡秘的雷同所震惊了。生态学中有种著名的现象叫做“拉波波特规则”:最大的生物物种差异存在于赤道地区,而越靠近两极,生物种类差异性越小。那么语言差异性特征是否也遵循这条规则呢?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伦敦大学学院的人类学家露丝·梅斯(Ruth Mace)与我一起对大约500个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美洲原住民部落进行了研究,并用这些样本所呈现出的不同语言种类数目与不同纬度上单位区域进行对应。研究结果表明语种分布情况与“拉波波特规则”完美相符。
生物物种与文化语言差异上所显露出的一致性或许并非只是巧合。要想在严酷的极地环境中存活下来,物种群落必须广泛分布,以避免其他物种的竞争,这对极北方的人类群落来说也同样适用。他们须要占据大面积的地理区域以保证食料的充分供应,而语言和文化也相应地广汇为一。另一方面,类似康丰富足、阳光普照的热带地区则成了物种分生的摇篮,繁荣的地貌环境使得当地人有条件拓建出大量情态迥异的社会群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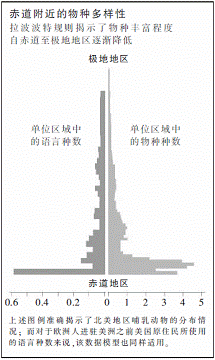
差异性与人类的结群与排外
当然,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人们会自愿分化成众多的小型群落呢?对于热带数以万计的物种来说,保持相互之间差异性的好处在于,这种差异性保证了各个物种在生态链条中的独特地位;但对于同处于生态链条中固定位置的人类来说,分化出不同的文化与语言共同体实际上毫无益处,其对于观念传播、技术交流与人口迁徙都徒增不便,甚至使得单个群落更不堪于风险和变故。那么为何不干脆整合为一个操着同样语言的大型群落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诉诸人类发展历史上持续不断的战争环境。自从我们的先人在大约6万年前走出非洲,人类就再未停止过领土与资源的争斗。我在《文化生成:人类社会思想的起源》(Wired for Culture:Origins of the Human Social Mind)一书中曾经提到过我们是如何习得那些帮助我们排除异己的本领。一为“结群(groupishness)”――与具备相同身份或特质的其他个体打成一片,二为“排外(xenophobia)”,将外于族群的他者妖魔化并加之于狭隘的地域歧视偏见。在这方面,语言在我们的群落认同过程中扮演着强大的社会性角色。我们说话的方式是一种持续性的对于自我认同的听觉提醒,同时也同样重要地警示着我们与其他群落的差异。
为了论证这个观点,我找到了一些人类学上的资料,一些部落仅仅为了使自己能够区别于邻近的群落便毅然决定改变其语言,并且效果立竿见影。举例来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支斯莱皮特语族群将他们表达“不”的语词“bia”改为了“bune”,以此来区别于邻近村落的其他斯莱皮特语群落。另一族群则完全颠倒了其语言中的阳性与阴性名词――“他”变成了“她”,“男人”变成了“女人”,“母亲”变成了“父亲”,依此类推。如果某个群落成员刚好在语言变更期间出门数日寻食猎物,那我们就只能对他表示同情了。
将语言作为身份标识并不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专利。无论何处的人们都用语言来识认与其同属一个“部落”的成员。我们对于周围人的说话方式十分敏感,有时甚至有些强迫症迹象,并且不断地用语言来将自身所在的族群与其他群落区分开来。能够与斯莱皮特语的例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能够将美式英语区分于英式英语的独特拼写――例如将像“colour”一类词中的“u”省去――几乎在19世纪初韦伯斯特所编著的第一本美国的英语语言辞典中一股脑地冒了出来。他坚持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我们的自尊与荣耀要求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系统,无论是语言还是政府。”
语言之分裂与消亡
利用语言来界定族群身份算不上是种新现象。为了厘清语言在人类历史中的分化演进过程,我和我的同事们拟出了一份三语系的谱系图――印欧语系,非洲班图语系以及源自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语系。这些“进化史”能够准确地将每个语系的发展历史追溯到其共同的发源,以此揭示出一种当代语言在其成型过程中与其他相关语言决裂“离婚”的次数。我们发现有些语言存着厚厚一沓离婚证书,有些则安分守己得多。
当语言发生裂变时,往往会经历一个短暂的快速更迭。同样的情况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也十分明显,我们通常称之为断续性进化(punctuational evolution)。因此一种语言发生婚变的次数越多,它与其源语言的词汇差异将越显著。我们的研究并未涉及一种语言缘何会一分为二。但十分清晰的是,语言变异的发生至少部分源于使用者对于自身同一性的诉求。我们身边正切切实实地上演着一场言语大战。
那么未来将会如何?我们当今处住的世界与我们祖先的栖居环境已大相径庭。在人类发展史上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里,人们只可能与那些保有相同文化传统的群落邻人打交道,而全球化与电子通讯的兴起意味着我们的交流与文化趋向阔泛与大同,这就使得相互理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而急迫。正如地球发展历史上大量的生物灭绝经历一样,趋同正使我们的语言也面临着同样的消亡境遇。
尽管现代语言并没有停下其进化发展不断裂衍的脚步,但少数民族语言的失落比率远远超过新生语言的冒露。随着小型部落社会中的青年人越来越热衷于对主流语言的使用,每年有30至50种语言正消失绝迹。从整体的比例来看,如此的消亡速率堪比甚至超过栖地荒竭与气候变化所导致的物种灭绝速率。在现存的约7 000种语言中,仅仅15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就占了世界语言使用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大多数语言的使用者均寥寥无几。
尽管如此,当今语言与文化的趋同演化速率还远远低于其极限,这归功于语言在标识我们的文化领土与身份过程中所起到的强大的心理辅助作用。可能导致的一种后果是语言拒绝来自于外来语种的“污染”,语言使用者总是对外来语词的渗入保有一定程度的嫌忌――看看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所谓的美国精神嗤之以鼻的态度便能窥出一二。另一个因素来自民族主义在努力拯救语言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威尔士在16岁之前的中小学生中普及威尔士语义务教育课程就是一例。
语言大同的未来
对于言语变革的抵抗为语言多样性的生发提供了充裕的空间。例如各式的街头与嘻哈方言对于某些特定族群来说,是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而爆炸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则使这些文化符号能够轻而易举地被定向至其自然受众。另外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世界语,作为一种精简的英语语言模式,其所依附的仅仅是1000个左右的词汇以及经过深度简化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在诸如外交官、国际商务人士等频繁辗转出行的群体中毫不费力地流行起来。有趣的是,英语的母语使用者在运用世界语方面往往并不占优势,因为他们所频繁使用的语汇和语法并不为其他人所理解。
从长远来看,某单一语种一统天下的情况貌似无法避免。以进化的角度来说,当几个同样优秀的方案竞争起来,总有一个会胜出。世界范围内诸如计时、测重测距、CD与DVD格式、铁路度量以及电力供应的频率等标准化模式无不趋于同一。尽管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语言的命运貌似也注定如是――所有的语言模式均可胜任信息交流媒介的角色,但总有一种会胜而为王。那么究竟会是哪种呢?
当今,约有12亿――每6个人中就有1个――中文普通话的使用者;西班牙语和英语以各自4亿的使用者位居次席;而孟加拉语和印地语紧随其后。这么看来中文普通话似乎会在角逐世界性语言的竞争中胜出。然而,绝大多数人选择将英语作为其第二语言。几年前,当我在坦桑尼亚的一个偏远地区试着用斯瓦希利语与一个当地人交流时,他挥挥手,示意我别费劲了,“我的英语比你的斯瓦希利语强多了”,他说。英语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内的通用语,所以如果让我押注哪种语言会最终胜出,我会押英语。
每一种语言在构建其独特的价值认同方面都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它是来自于人心灵深处寄托着记忆、思想、希望与忧虑的独特声音。失去了语言,便失落了这一切珍贵的财富。
但是,我认为一个单向度语言的未来世界并不会如同灾难预言者所展示的那样糟糕。很多人坚信,使用的语言决定了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因此语言多样性的泯灭意味着独特思维方式的失落,对于这一点我并不苟同。我们的语言虽然决定了我们所使用的语汇,但却并未限制我们赖以了解与感知世界的诸多观念。另外,我们也许能从巴别塔的故事中参透出别一种更为积极的价值导向:语言大同的一天,人们将变得更为协作团结,以期成就前无古人的不朽伟业。毕竟,当今世界正是那些拥有最小语言差异的国家取得了最为令世人瞩目的繁荣成就。
资料来源 New Scientist
责任编辑 粒 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