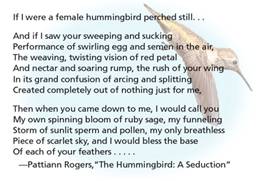为了准确地表达生态系统中各介质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可能需要打破传统的科学语言。

为了在长距离飞行中一直保持在高空,信天翁利用了盛行风的剪力和由不停流动的水推动形成的空气膨胀。鸟类、空气和水都在同时移动,在相互依赖的循环中互相作用
我们的语法教给我们的是把世界分成主动的主语和被动的宾语,但在一段协同进化的关系中,每一个主语都是宾语,每一个宾语也都是主语。
――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植物的欲望》
很难想象在现代科学中还有比“相互依存”渗透性更强的理念,这是理解各种系统的关键概念,尤其是像这样活生生的生态系统。不同的个体以多种方式同时交互:想一想在一个生物群落里所有的小生物都在对其他生物和整个系统做着各自不同的事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有很多不同音调的管弦乐队在胡乱弹奏着,持续不断地影响彼此。在音乐中这被叫做“复风格”。但当人们尝试定义生态系统中不同的组件是如何工作时,科学语言更倾向于集中关注一个个体,追踪它的系列活动,但在这个过程中恰恰丢失了相互依存的精髓。
为学术期刊撰稿的专业科学家和大众科学写手都追随一种传统的写作规律,正是这种规律引发了问题。在一份典型的高校为科学写作提供的指导中,会列举出好文章的几大原则:清晰、简洁、公平、逻辑性强、准确以及客观。它可能还会警告学生,有些科学家的写作习惯会让作品变得乏味难懂:要避免用被动语态、过去时和过长的句子。一个关键原则是要避免个人感情:写作者应当将他们自身和他们的个人情感完全置于文章之外。
这种语言在描述生态学过程时就变得不合适了。如果说当代科学的使命之一是要教育大众万物都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新语言的帮忙。唤醒对多层面现实的感知,捕捉它的奥秘,用例子来展示它是如何工作的,尤其是回到相互依存的观察者本身的需要,开始建议我们需要转移关注点。更近一步说,用一种新的生态学语言来描述事物,可能会向我们展示出普通观察不能展示的科学过程和交互现象。新概念会激发出新感觉,新的表达方式能让我们对现实有新发现。
没有什么比描写鸟类的文学――不管是科学还是诗歌――更能体现这种表现相互依存的新语言的美了。以A.J.瓦德-史密斯(A.J.Ward-Smith)1984年所著的教科书《生物物理空气动力学和自然环境》中对信天翁飞行的描述为例,他在书中尝试分析不同的飞行生物和它们运动的空气间的交互关系。为了能在南冰洋上空轻松不间断地长时间飞行,信天翁使用了一种不需要依靠上升气流的翱翔方式――一种被瓦德-史密斯称作“动力翱翔”的独特飞行方式。这种鸟转着圈以椭圆形逆风上行并慢慢停止,接着向下滑翔并加速,最后还要在减速的同时避免撞击水面。但在绘图并提供详细的数学证明后,作者在一小段结语中承认他并没有完整地讲述整个故事:
尽管把海面作为一个平面来做数学分析会很方便,实际上风的作用会让海面有很大的起伏。在这样的情况下,信天翁用“斜坡翱翔”的技巧靠近波浪飞行会让它“动力翱翔”的技巧得到更有效更普遍的应用。
换句话说,信天翁做到的比“动力翱翔”更多一点;这种鸟也会在重塑海平面的风力膨胀中“斜坡翱翔”来汲取更多能量。我们没有必要打比方说信天翁在风中和水浪推动的空气中冲浪和翱翔。这里我们介绍一种可以为科学分析所用的类似诗歌的语言。一个热爱科学的诗人可能会更进一步,将词语组合成混合词,例如“冲翔”(soarf)。科学界本身也有很多这样组合成的词语,像烟雾(烟和雾)、受控机体(受控的机体)或者正电子(正的电子)。为什么有“科学诗歌”(scipoe),不能创造“冲翔”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更深入地去探查,信天翁的行为是否会影响风浪运动的力量和形态本身,即使只是微小的影响?这会是一个由文学词汇和新概念引发的、对这个小的离散系统更新鲜更综合的感知。
在另外一本流行教科书《鸟类的生活》中,鸟类学家乔尔·卡尔·韦尔蒂(Joel Carl Welty)激烈地――我认为也是很成功地――挣扎着描述,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拍翅飞行。


北部的赤耳金翼啄木鸟像扇子一样打开翅膀和尾巴,这让它的翅膀中间上推的空气中获得更多的升力。如果不翱翔,它们不会对气流有这样动态的应用
一个普遍的认识是,拍翅是一种通过蛙泳动作向下推动在空气中支撑住鸟类,向后推动让鸟类前进的动作。这个认识是错误的。当一只小鸟起飞的时候,翅膀会在下方前后移动。因为翅膀的尾部没有前部硬,尾部会在气压作用下向上弯曲,将整个翅膀变成一个可以将鸟向前拉入空气中的螺旋桨。
在为了达到清晰而努力的时候,韦尔蒂错过了最重要的一点,这种鸟并没有像他所写的在空气中“游泳”,只是在抬升它自己或是被翅膀下形成的增加的空气压强抬升。他让鸟变成了独角戏演员,但事实上被鸟搅乱的空气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鸟将空气向下切成了片,并用它弯成弓般的翅膀上下反复在空气中摩擦出嗖嗖的声音,用“二面角效应”来提升它在空中的高度。如果尝试换一种简洁的诗歌化表达,我们可以说这种鸟通过减轻上部空气来“发射自己”,或者说它通过从上部压强较小的空气中上升来“向上减轻”它自己,同时下方形成的从后方推动的气流将它向前“猛推”。我们几乎不能用语言来记录下相互作用的过程,鸟类间的互动、翅膀形状和空气。但有趣的新词汇和半喜剧性的双关语能激起人们对简单鸟类飞行更深入的审视。
可能对鸟类飞行最夸张的描述来自诗人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y Hopkins)在《茶隼》中对隼飞袭的描述。
我捕捉到了这最初的清晨的宠臣,
白昼之王的太子,
这黎明勾勒其斑纹的鹰隼,
它骑乘在那被稳定的空气托举的旋转平面,
在高处大步前行,
看吧,它那折叠起翼翅之缰的陶醉忘我的盘旋!
接着向前,飘荡,飘荡在秋千上,
就像冰鞋的后跟滑出一道弯曲的弧线,
在俯冲与滑行中抗拒着大风。
――杰勒德·曼利·霍普金斯,《茶隼》片段(张祈译)
当隼飞袭的时候,它的下坠暴露在了霍普金斯这个神秘的僧侣观察者面前,基督在捕捉灵魂方面的能量让他兴奋到疯狂。霍普金斯看起来除了希望能同时以现实和象征手法描绘出隼的俯冲过程外,对科学探究极度反感。所有的词汇、短语和论述,以及韵脚、重读和诗的形式都表达了极其复杂的意思。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自然中的形而上学,现实生活中的神圣――但最重要的是,也帮助我们达成了目的,表现了鸟类和自然的交互。
在最开始的时候,霍普金斯在标题中通过英语词汇“风中盘旋者”来表达“隼”,从而巧妙地定义了隼和空气系统的交互性。“风中盘旋者”本身不仅有风从中穿过的意思,它本身的词义也是一个“风中翱翔者”(wind hover-er)。隼是“黎明时划出的斑纹”,日出时它们常常出来打猎,此时天空和鸟身上的图案都因为太阳的效果被拉长了。它驾驭的空气有时会“平静”和“滚动”,为它的盘旋提供了升力,同时鸟也喜欢平静的滚动的空气。

三个雄性野鸭(右侧)一直在对左侧的雌性求偶;当她起飞的时候,三只雄性几乎同时都准备跟随

为了从它飞行的海洋空气波中得到推力(也为储存自己的能量),闲逛的信天翁必须向下滑翔,将它带到危险的离水面足够近的地方
隼在看起来能“驾驭”风飞翔,将自己稳定在由看不见的暂时形成的空气动力场中。它的翅膀就像空气一样在“荡漾”,或者像流动的一小股水流一样在旋转。隼在风流中“盘旋”,就是随着风绕着圈飞行,可能在是在用这种象征性的行为来捍卫自己,就像在空中摇铃一样。接着它会向下俯冲,这时它形态的比喻也改变了,它像一个滑冰者在冰上划出弧线一样在空气中滑翔,但隼仍然会在空气中投掷自己,断然拒绝扑面的和在俯冲过程产生的风。风和鸟几乎合成了一体,同时自然的准确性和神秘的暗示也结合在了一起。
生态学语言给科学带来的益处
这种写作可能给科学带来的好处是它揭示了鸟类在静态和动态阶段的能量,从俯冲急剧变化到滑翔的方式,空气在每个阶段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描述它,但要揭示它并用模仿性的语言来表达它就需要在原本直接和感性的维度上增加更多深层次的审视。
兴奋常常在科学写作中被看做是令人生厌的,因为它会让作品中突然出现科学观察者的感情。人们不能轻易放弃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对科学的客观性,但常常是这种冷漠的、毫无激情的立场会让人们得不偿失。一段保守生物学家格温达·布鲁尔(Gwenda Brewer)对野鸭交配习惯的描述就能很好地体现这点。
布鲁尔小心地避免了对雌性和雄性彼此间含情脉脉的行为的拟人化描述。她对这个精心的性仪式避开了个人看法和感情,并且避免了表达鸟类这种行为所要传达的意义。两只鸭子变成了分离的、几乎机械的个体,一个是另一个的“目标”。她强迫自己的客观性,使用别扭无趣的术语,用被动语态混杂着引用,将前戏的过程完全模糊化了,似乎鸟儿们对彼此完全不感兴趣:
在翅膀后面打扮自己之前只是用嘴巴沾点水并摇摇头,尾巴常常在展示之后摇一摇(展示给河对面的目标看)。如果距离较近,当雄性将翅膀啪地打开时能听到尖锐的呼呼声,接着雄性就会把嘴放在后面或是放在翼斑上。雄性有时在他们表演在翅膀后面打扮自己之前会吱吱地叫。将头转向后面被看做是很少见的。雄性会在河对岸对目标鸟表演一种夸张的抖动。
布鲁尔乏味的散文,关注在每一只单独的鸭子上而没有注意到他们之间的互动,从没去欣赏鸟儿们正在进行最具交互性的过程,我们也无法感觉到当地的水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种沉闷冷漠的方式缺少了生态学的愿景和语言,所以也不能引起人们提出关键科学问题的好奇心:为什么他们要对对方做出这样的举动?
与之截然相反,诗人帕蒂安·罗杰斯(Pattiann Rogers)在《蜂鸟:一种勾引》中将她自己想象成了雌性蜂鸟,一只有人类意识的鸟,为雄性着迷,眼花缭乱并最终被一只雄性勾引进行了交配。
如果我是一只正在栖息的雌蜂鸟……
我看到你在梳理和正在吮吸
空气中纷飞的精子和卵子,
编织缠绕的赤色花瓣,
花蜜和高耸的臀,你翅膀急剧地扇动,
制造了弧线和裂纹的一场巨大的混乱,
这无中生有的一切都只是为我
而当你向我飞来时,我会呼唤你
我自己旋转绽放的红宝石般的鼠尾草
我汇集的阳光下的精子与花粉的风暴,
我无法呼吸的
惟一的淫荡的天空,我会祝福你
每一片羽毛的底部……
――帕蒂安·罗杰斯,《蜂鸟:一种勾引》(张祈译)
这些性幻想都能在现实中红喉蜂鸟的交配习性中找到根据,雄性会从高空俯冲向静静地坐着的雌性,在她周围划出一圈一圈的椭圆形并闪着颜色。诗人增加了想象并将雄性的展示描述成性和生殖的“暴风雨”,揭开了它下降过程中接近攻击性的特征,但同时也使用了完全想象中的比喻―“空气中纷飞的精子和卵子”,“阳光照射的精子和花粉”――用局部表现了整体。这让跳跃的雄性、鸟类精子和植物花粉一起同时代表了雄性和雌性的性精髓。罗杰斯将两只鸟的性欲、雄性的行为、代表颜色展示和性冲动的花融合在了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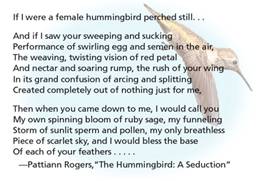
诗歌语言传达了主体、气氛和相关特征的交互过程,直到鸟看起来像是用自己的性冲动把空气都染上了颜色,就像罗杰斯把他叫做她的“无法呼吸的/惟一的淫荡的天空”。除了想象中的好色之徒,我们还读到并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了生动的蜂鸟交配行为,这种理解能给我们带来和诗人、和科学家类似的深刻洞察力。
科学可能会回避这样的语言,将它当成对核心概念的扭曲。但当核心概念逐渐形成,生态学模型占据重要地位的时候,也需要发展一种更具交互性的表达方式。解释生态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应该很简单:一个生物体存在、行动,导致其他东西也变化或应答,第一个生物体首先做出反应,之后的会接着做出。然而现实中很多不同的个体以复杂的方式多方向,同时交互。
视觉展示能帮上忙。在学术语言中,生态系统的交互性常常被描述成一张网,或者是有多重向量前后指向系统中不同成员的图表。也许未来的科学家可以用动画来表现所有这些效果是同时出现的,每个个体都在受其他所有个体的影响,像在表演一场神秘的精心设计的芭蕾。但即使这样,更加诗意的语言也是有用武之地的。
或者,让我大胆地建议,整个生态系统的解释工程都可以用释义乐声来完成,就像科学的复风格!崭露头角的科学艺术作曲家,你们会成功的!
资料来源 Americ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彦 隐
――――――――――
本文作者罗伯特·路易斯·查尼斯(Robert Louis Chianese),美国加州大学北岭分校英语系荣誉教授,1979年米切尔可持续奖获得者,2012年曾担任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太平洋分会主席,是100年来担任该职位的唯一人文学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