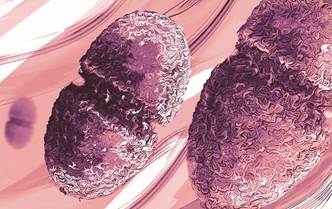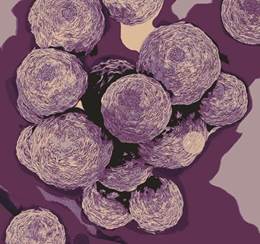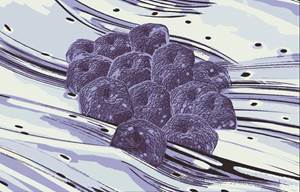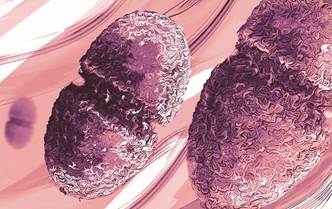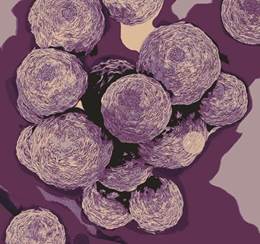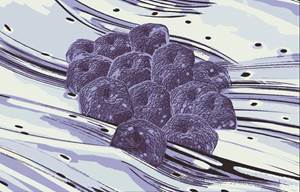抗生素耐药性的威胁已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很少有人注意不到。最近几年报纸上的头条新闻都在警告潜在的“抗生素灾难”,抗生素问题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难题,或者至少充满了危机。这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知晓这个问题的人越多,人们就越担心。目前,耐药性细菌感染每年导致70万人死亡,其中90%以上都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患者,据权威人士预测,到2050年,这一数字可能会上升到1000万人,多于当前死于癌症的人。
几乎从抗生素时代伊始,人们就发现了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早在1945年初,青霉素的发明者亚历山大·弗莱明就认识到,过度使用抗生素可能导致细菌产生耐药性。他曾对《纽约时报》说过,“那些不经慎重考虑就轻易给病人使用青霉素的人,要为一些最终死于感染的人负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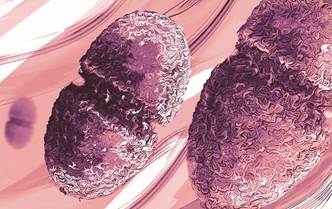
ESKAPE病原体列入了寻找新药物的优先级名单中,图为屎肠球菌
自2010年以来一直任英国首席医疗官的莎丽·戴维斯(SallyDavies)是呼吁人们重视抗生素抗药性问题的强力倡导者之一,也是2014年向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提出对抗生素问题进行大范围审查的呼吁者之一。两年后由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O’Neill)主持制定的审查方案提出了减少抗生素威胁的10个具体步骤。许多国家现在都提出了有雄心的行动计划,联合国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戴维斯对目前的应对措施仍然不满意,“我们需要加大应对力度。”她说。
有好几个组织已经列出了“优先级病原体”的名单――耐药性问题最严重、对新药需求最为急迫的细菌种类。美国传染病协会列出的几种优先考虑的细菌为:屎肠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杆菌(佛里德兰德氏杆菌)、鲍氏不动杆菌、绿脓杆菌和肠杆菌,按其首字母缩写被称为ESKAPE病原体(抗生素失效病原体)。世界卫生组织列出的10个抗生素失效病原体名单根据其构成威胁的严重程度分为威胁最严重的和除了金黄色葡萄球菌外的其他所有ESKAPE病原菌。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列表中几乎所有的病原体都是具有双层细胞壁的革兰氏阴性细菌,小分子很难穿透这层细胞壁墙,因此这些细菌也是靶点设计药物最难对付的。
资源和资金不足问题
一种成功的抗生素必须能够杀死细菌,或者至少可以阻止它们继续繁殖,同时对人体的伤害要达到最低限度,因此它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人体细胞没有的分子靶标或机制。它们或者专门针对细菌的某种独特性,例如它们的细胞壁,要么针对细菌与哺乳动物完全不同的结构和机制,有选择性地加以消灭。抗生素的最大类,以其紧凑环形结构命名的β-内酰胺属于第一类,它们通过抑制细胞壁肽聚糖层的形成,破坏细菌细胞壁合成。与细菌核糖体结合并以其蛋白质合成为靶标的药物属于第二类。
抗生素耐药性的历史远比人类发明甚至改进抗生素的历史更悠久。数十亿年来,细菌一直在进化,以保护自己免受有害物质的侵害,这种耐药性会迅速蔓延开来,主要是通过生物体之间的所谓“横向”基因转移。最常见的三种机制包括破坏抗生素分子本身,修改靶蛋白导致药物无法与其结合以及在药物生效之前将其从细胞中逐出。
如果有许多新的抗生素连绵不断地生产出来,那么过去和现在对抗生素的耐药性都会大大降低。然而现实远远不是如此,近几年由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注册的新的化学实体(NCEs)中,抗生素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且都是药物产业中所称的“跟风药物”,即创新仿制药:对现有的化合物进行研究做一些小的调整修改开发的所谓新药,例如,减少副作用,或针对细菌抗药性提高药物性能等。具有新靶点的抗生素,甚至绑定同一标靶但作用机制不同的药物将很难被细菌击败。但从抗生素开发历史看,这样的例子很少,而最近几十年来根本看不到了。
不言而喻,抗生素发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大量训练有素的科学劳动力。然而这些年来,大型制药公司纷纷退出抗生素市场,转而在慢性疾病药物的开发中寻找发现更大更有把握的利润空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抗生素研究和开发进行的调查表明,2016年英国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工业科学家不到150人,Redx制药公司关闭了其抗感染药物分部,阿斯利康公司将其抗生素研究业务卖给了辉瑞之后,其中至少有40人失去了工作。相比之下,只有一个慈善机构――英国癌症研究中心有大约4000名研究人员还在支持抗生素研究。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大致相同,临床实践中也有类似情况。在美国,传染病医生的报酬比其他任何医学专业都低,而且越来越难以填补人才空缺。因此,奥尼尔的评论以大幅标题提出“提高感染疾病医护人员的人数、收入和认可度”也就不奇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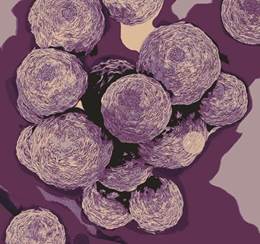
ESKAPE病原体:金黄色葡萄球菌
抗生素开发中的携手合作
一些经常与学术机构开展合作的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如今正在进军制药巨头空出来的缺口,并最终获得大量支持创新发展计划的资金。例如,2016年的CARB-X计划是由美国卫生署和英国威康信托基金会提供资金资助的,预计5年内投资10亿美元,以加速至少20个瞄准最重要耐药菌新项目的开发,包括新抗生素、新诊断技术和新疫苗。“目前只是前期阶段,但我们已经投资了24个项目,涉及10个新分子靶点。”CARB-X计划执行董事凯文·奥特森(KevinOutterson)说道,“我出生于最后一种用于治疗革兰氏阴性菌的抗生素类药物获得批准的年代,因此如果我们的项目技术有一个获得审批通过,也将是我一生抗生素研究的最大转机。”
英国的抗菌素耐药性研发中心(AMR中心)建立在英国柴郡的阿尔德利园区,之前是阿斯利康公司所在地。2016建立的AMR中心与CARB-X有着相同的目标,但规模要小一些。AMR中心计划于第一年投入600万美元,重点放在世卫组织列出的“关键”病原体上。“我们的投资有可能就一致性的目标与CARB-X开展广泛的合作,但在投资组合方面会有所差异。”AMR中心执行主任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说道,“与CARB-X不同的是,AMR中心有自己的实验室,因此我们为规模较小的公司提供他们可能需要的设施,例如,药物代谢和毒性试验、配方或体内研究等,稍后我们还将进一步参与药物发现的过程,从方案优化到II期临床试验。”
这些以及其他类似的举措有助于增加参与抗菌药物研究的科学家数量,并有助于实现奥尼尔提出的以研究为基础的两个提议,“(建立)早期和非商业研究的全球创新基金”和“(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促进新药投资、改进现有药物”。令人鼓舞的是,抗生素的开发渠道终于开始扩大,更多的新分子正在通过早期阶段。
CARB-X和AMR中心还为企业投资网络、共享信息和资源提供机会,公司之间的合作正在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一些医学治疗领域,如预期经济回报率很低的传染病领域。共享数据进一步促进了合作,如今抗生素研究可以通过一个新的数据共享平台获益,即皮尤慈善信托基金的抗生素研究和知识共享平台(Spark)。这一平台使用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家国际软件公司“合作药物发现公司”的技术。“我们的平台CDD-Vault为药物发现提供了一个完整、安全的信息接口,公司和他们的合作院校可以通过这个平台,与他们选择的合作对象和合作方式共享数据。”该公司英国剑桥办事处的玛丽安娜·瓦切托(Mariana Vaschetto)说道。
牛津抗生素开发的悠久历史

ESKAPE病原菌:肺炎克雷白氏杆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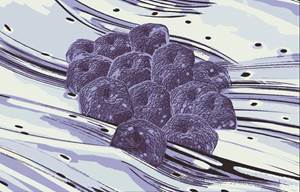
ESKAPE病原体:鲍氏不动杆菌
很少有学术机构像英国牛津大学那样有着悠久而富有成效的抗生素研究历史。与弗莱明和恩斯特·钱恩(Ernst Chain)分享1945年诺贝尔医学奖的霍华德·弗洛里(Howard Florey)在病原体研究领域内也有一席之地。在爱德华·来伯拉罕(Edward Abraham),杰克·鲍德温(JackBaldwin)以及如今的克里斯·斯科菲尔德(ChrisSchofield)的主持下,青霉素化学的研究在牛津大学一直延续至今。还有几乎被人遗忘了的多萝西·霍奇金(DorothyHodgkin)也是牛津大学教授,为她赢得1964获诺贝尔奖的,不是著名的胰岛素分子结构研究(胰岛素分子结构直到1969年才完全被破译),而是对维生素B12和青霉素结构的测定。
斯科菲尔德研究小组目前的工作重点是了解许多细菌中β-内酰胺酶的结构和机制是如何进化以对抗β-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它们都是通过破坏抗生素的环结构导致无效,但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机制。市场上的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克拉维酸(与阿莫西林素结合形成复方阿莫西林)与丝氨酸蛋白酶有着抑制β-内酰胺酶的相似机制。
现有药物中还没有以另一类β-内酰胺酶为靶向的,其基本机制与金属蛋白酶相同,唯一能应对“β-内酰胺类最后手段”的,是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我们正在寻找抑制金属β-内酰胺酶被称为NDM1的化合物,目前已在革兰氏阴性细菌中发现,对几乎每一种现有的抗生素都有抗药性。”斯科菲尔德研究组中的博士后尤尔根·布雷姆(Jurgen Brem)说道。“在与欧盟创新药物计划的合作中,我们已经开发出了一些很有潜力的化合物。”下一步将通过动物实验对这些化合物进行测试。
牛津大学创办了许多成功的公司,其中一个是牛津药物设计,重点是新型抗生素。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这一年inhibox公司将化学家格拉哈姆·理查兹(Graham Richards)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成果实现了商品化开发。最初它只是一个计算化学咨询公司,后来随着重心转移到发现新抗生素后改为了药物设计公司。“我们已经加强了专门研究细菌渗透性的基本化学信息学技术部门的力量,用以设计抑制细菌tRNA合成酶的分子,从而抑制其蛋白质合成。”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费恩(Paul Finn)说道。
就像细菌核糖体一样,细菌tRNA合成酶与等效的哺乳动物酶完全不同,从而可以设计出选择性抑制剂。它们并不是完全的新目标,唯一的一种针对tRNA合成酶的抗生素莫匹罗星(外用抗感染药)已在市场上有售,这种抗生素代谢迅速,因此只能用于治疗皮肤感染。“我们开发最好的化合物可以抑制具有低纳米效力的靶向合成酶,并杀死ESKAPE病原体。系统性感染动物模型的研究现在已经开始了。”费恩补充说道。
在旧药基础上的创新
为某种目的研制的药物有时可用于不同的目的。2010至2013年间,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一组科学家筛选出了一个大型化合物库,其中包括抗药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许可药物,并提取出了金诺芬,一种有机化合物,是FDA许可用于治疗关节炎的药物。这些令人惊讶的发现促成了Auspherix公司的创办,该公司总部如今设在英国的斯蒂夫尼奇,并正在对一系列化合物进行优化,这些化合物基于一个类似的支架,中间有一个金原子。
这些化合物可以杀死优先级名单上的许多耐药细菌,而且重要的是,它们已被证明可以破坏细菌的生物膜。这些细菌聚集在黏性细胞外基质上,通常附着在表面上,它们对大多数抗生素和人类免疫反应都有抵抗力,因此很难根除。“我们已经确定了从发现到临床应用的路径,并且最初将重点放在治疗复杂尿路感染的化合物上。”Auspherix首席执行官理查德·鲁特(RichardRutter)说道,“我们已经为我们开发的分子设计了一个临床开发途径,但我们还没有确定它们杀死细菌的确切机制。”

ESKAPE病原体:绿脓杆菌
到目前为止,CARB-X已与三大洲6个国家的一些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亚洲唯一与其合作的企业是总部在印度班加罗尔的Bugworks公司,预计不久CARB-X将宣布投资亚洲其他企业。“我们没有特意寻找印度公司,但就优秀的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而言,Bugworks符合所有的要求。”奥特森说道。Bugworks的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了一种新颖的“隐形”策略,用于防止抗生素从细菌细胞中排出。“我们的策略是选择一种可针对细菌特定‘外排泵’,以及通过基于结构的方法与其结合的有效分子,并希望这些分子能在2019年进入I期临床试验。”Bugworks研发部门负责人维·巴萨布拉马尼安(V.Balasubramanian)说道。
与Bugworks,Auspherix以及牛津药物一样,其他许多公司开发的临床前候选抗生素似乎也大有希望。开发的最初阶段比较顺利,但之后可能还会遇到一些问题。“据估计,早期开发的化合物只有70种会得到许可。”奥特森说。一些公有民营的小公司,通过慈善基金的资助可能会将某种分子投入早期临床试验,但随后的试验将更昂贵更具挑战性,而且风险也更大。大多数人认为,那些能够将抗生素部门维持下去的大型制药公司(如默克)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仍需要收回成本。对于临床医生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作为最终手段的药物”,但是有哪家公司会为这种销售量有限药物的开发投资数百万美元呢?我们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筹资机制:也许是一种非常慷慨的一次性现金奖励,让开发商能够以成本价出售药物。一个现有的例子是为准确的、负担得起的细菌感染诊断试验颁发的经度奖。
那么,在抗生素与细菌抗药性的斗智中,我们能否胜出?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分子生物学家乔舒亚·莱德伯格(JoshuaLederberg)的话,“这需要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跟上(细菌)基因的进化。”希望不再缺少源源不断的新抗生素分子,但这需要我们所有的想象力和政治意愿,以及资金问题的进一步改变,将其提高到目前癌症研究的水平,获得足够的资金。所有这些都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要在与抗生素耐药性的赛跑中取胜,我们就必须更加谨慎地使用我们现有的药物。
资料来源 Chemistry World
责任编辑 彦隐
――――――――
本文作者克莱尔·桑塞姆(Clare Sansom)是英国伦敦的一位科普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