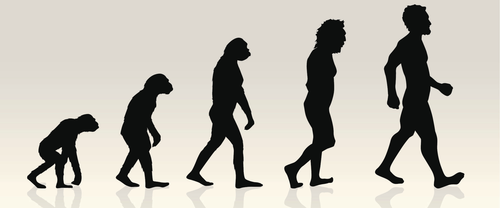《创建未来》一书探索人类预见未来的变革性力量,探讨其对进化产生的影响。
《创建未来:预见的自然史》,托 马斯·苏登多夫、乔纳森·雷德肖、亚当·布里著,基础图书出版公司,2022年9月出版
佛利伍麦克合唱团(Fleetwood Mac)在一首金曲中唱道:“不要停下,想想明天/不要停下,它很快到来。”这条建议其实有些多余,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明天。我们花费大把时光想象明天、下周甚至明年要做些什么,以至于认为这种能力理所当然。在想象的天地中,许多人对未来展开想象,如同回忆过去一般轻而易举。
心理学家给这种在大脑里畅游时间的能力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心理时间旅行”。
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多数动物没有能力(至少不能如同人类这般)进行心理时间旅行。婴幼儿以及特定认知障碍的患者,如进展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没有这种能力。但有证据显示,我们种群的多数成员至少从直立人时期就能够在脑海中进行时间旅行。认知科学家托马斯 · 苏登多夫(Thomas Suddendorf)、 乔纳森 · 雷德肖(Jonathan Redshaw)和亚当 · 布里(Adam Bulley)在新书《创建未来:预见的自然史》(The Invention of Tomorrow: A Natural History of Foresight)中指出,心理时间旅行使一切发生了改变,发展出回忆过去事件时对未来进行预见的能力是人类种族进化的关键。
作者在书中主要关注想象未来的能力,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和回忆过去紧密相连。根据作者的研究,儿童在回忆过去和描述未来计划的能力间存在关联。亦有其他研究显示,随着人的年龄增长,回忆过去和想象未来的能力以相等的速度减退。
有趣的是,我们的记忆并非一直准确——至少不会同我们想象的那样准确。但作者认为这种不准确性有时无关紧要。记忆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使我们为未来做好准备。书中提到:“自然选择并不在意你的记忆是否能够准确地反映过去。真正重要的是记忆对生存和繁衍带来的影响。记忆是为了未来。”
有不少观点猜想使人类种族产生“优势”的关键因素到底是什么。在人类学家和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 · 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2009年出版的《点火》(Catching Fire)一书中,他提出烹调食物是人类走向世界主宰的重要推动力。已故生物学家爱德华 · 威尔逊(E. O. Wilson)在多本书中强调社会行为与合作的重要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使用工具或是语言才是发展关键。
苏登多夫和同事们并不认为这些是错误答案,但他们将预见能力作为这些的基础,或至少存在紧密联系。举例来说,设想直立人在近200万年前开始使用“制作精良”的手斧(尽管在我们眼中还是相当粗糙),使用这种工具需要对计划和执行进行预见,作者认为人类的这种预见能力比其他动物要强大得多。同时,这种斧子似乎会被远距离携带且多次使用。
作者对预见和掌握生火的技能做出了类似的论断。同时认为预见对语言的意义更为显著,他们认为语言使我们能够与周围的人更好地交流一些灵感和计划。“这种交流,”他们写道,“使我们更好地做出预见并协调行为,使未来更加接近我们的设想。”
其实这一联系可能更加密切。作者指出,语言学家指出人类语言的关键特征之一在于语言的移位性:一种“指涉遥远时间和空间中事物”的能力。这对于并非专家的我而言,很像是心理时间旅行。我们很难将人类在星球上的统治力归因于单一的能力,但许多人类技能确实无法脱离预见而实现。这种论断看似可靠,但需要指出的是万物皆不能凭空而立:语言需要预见,而预见需要的则是抽象思维,抽象思维则需要大脑建立合适的神经连接……那么其本源基础又何在呢?
作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预见以何种程度将我们和动物界的其他生物区分开来。粗略来说,其他动物看似几乎完全生活在当下,而人类的意识则能够在既存的时间轴上自由来回。“迄今为止,”他们写道,“我们没有证据表明其他动物能够利用沟通交流共同进行一场记忆之旅,或是一起描绘未来场景。”他们相信“人类构建心理情境的能力有独到之处”,同时能够将这些想象之物与其他人类共享。
但非人动物是否真正被困在当下呢?一些动物表现出能够进行一定程度构建未来的行为,譬如松鼠埋藏坚果以预备过冬。但作者指出这种行为是本能的。“年幼而未经历过冬天的松鼠也会收集并贮藏食物,”他们写道,“说明这种行为是由本能而非洞察所产生。”
除此之外,作者在书中详细地讨论了近期一些记录各类物种表现出一定程度预见或计划能力的研究。作者承认一些动物具有长程记忆,且能够从中学习,但他们仍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其中一例是剑桥大学心理学家妮可拉 · 克莱顿(Nicola Clayton)和同事们进行的灌丛鸦研究,这种鸟类习惯性地为未来的进食藏匿、储存食物。但它们也能够根据储藏和进食间的时间间隔调整觅食策略。
举例来说,如果灌丛鸦同时贮藏黄粉虫幼虫和坚果,且能够在数小时内到达两种食物的储藏地,它们会更倾向于找回虫子作为食物,因为它们更喜好这类食物。而如果储藏行为已经过去了5天,那么它们就会去找回坚果——似乎是知道虫子经历长时间后会发生腐败。2007年,克莱顿和同事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西部灌丛鸦为未来做打算》(Planning for the Future by Western Scrub Jays)一文。
这一发现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但苏登多夫等人认为这并非体现了预见的能力,而是“反映了联合学习”。由于记忆随着时间消退,灌丛鸦“可能学会了将食物位置的记忆强度和回收食物时的味道进行联系”,这揭示了灌丛鸦的行为“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贮藏食物时需要心理上的重新审视并进行预见”。
苏登多夫和同事们似乎更看重那些体现人类独特性的研究,而轻视了体现非人动物能力的部分,因此读者会猜测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偏差。但说到底,争论心理时间旅行是否为人类独有,或非人动物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这种差异或大或小,总是存在的。作者提醒读者的事实则是需要合理看待人和其他物种间的“鸿沟”:如果曾经同我们共享这个星球的人属生物依旧存在,智人和其他动物的差距似乎就不那么大了。如果直立人仍在山中用斧头劈下鹿肉,尼安德特人还围着篝火讲着故事,我们会意识到智人的能力尽管令人惊叹,却也只是谱系中的一分子。
资料来源undark.org
——————
本文作者丹·佛克(Dan Falk)是驻多伦多的科学记者。他的作品有《莎士比亚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hakespeare)和《探索时间之谜》(In Search of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