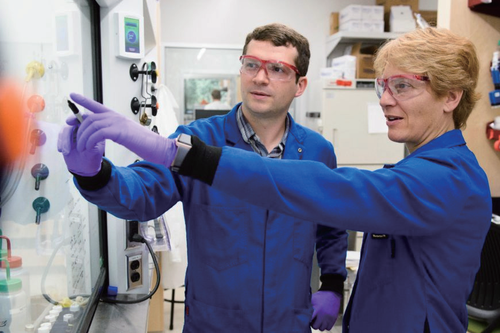美国化学家卡罗琳·贝尔托西表示,自己几乎就是凭借“潜意识”走上科学之路的。2020年3月,贝尔托西凭借其首创的可在活体细胞内进行的生物正交化学反应,获得了索尔维未来化学奖
卡罗琳 · 贝尔托西(Carolyn Bertozi)的父亲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但她进入哈佛大学后,一度想主修音乐。“我父母不希望我这么选择。我的一个亲戚从事音乐事业,最后却通过在银行上班来付房租。我不太敢违抗他们。”于是她选择了包括数学和科学课程在内的医学预科课程,并在大一结束时决定主修生物学。她表示:“我在大一并不喜欢普通的化学课。它只是我必须打勾的一个选项而已。”
使得贝尔托西意识到化学之趣是第二年的有机化学课。她打趣道:“同学们对这门课的评价是‘教授简直在故意为难我们,同学们抱怨要背的东西太多,但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它,我丝毫不觉得有机化学繁琐或怪异,它匹配上了我的大脑。’”
一年后,贝尔托西从生物转向化学。当然,音乐事业并没有半途而废。当许多同学在餐馆做服务员以支付大学费用时,她在重金属摇滚乐队里演奏电子琴并伴唱。那是20世纪80年代,她所在的乐队经常在大学派对等活动中演奏自己的金属摇滚或流行歌曲。
寻找实验室的本科生
哈佛大学鼓励理科学生在暑假期间去实验室工作。贝尔托西回忆道:“大二结束后,我想去有机化学实验室做研究,但他们都说已经满人了。”她最终去了马萨诸塞州眼耳医院的实验室研究氧化膜损伤问题。其间,她每周都跟着艾琳 · 科切瓦尔(Irene Kochevar)教授学习,带着一堆硬币,去近5公里外的医学院图书馆复印论文。
美国著名摇滚音乐人汤姆·莫雷罗(Tom Morero)曾与贝尔托西身处同一支乐队
卡罗琳·贝尔托西从2015年开始进入斯坦福大学工作
当时,激光眼科手术还是一个新鲜事。贝尔托西表示,了解眼部组织会否被手术激光损伤很重要。她通过特殊的摇动方式把膜取下,然后用激光照射它们,看看它们红细胞中的“鬼影”会不会因此被去除。
不久后,贝尔托西的化学之路迎来转折。“我学习了物理有机化学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也结识了一些毕业生,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我本以为他们可能会向我介绍他们的首席研究员(PI),这样可以帮助我获得暑期实习机会,但实际上并没有。我开始觉得成为有机化学家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
贝尔托西先是在生物化学实验室找到了一份工作,然后又遇到了当时正教授研究生课程的物理化学助理教授乔 · 格拉博夫斯基(Joe Grabowski)。格拉博夫斯基的实验室只有一名毕业生——因为他的教授类型决定了他获得终身教职的可能性很低,鉴于这位教授长期前景的不确定性,毕业生们往往不愿意拜其门下。
格拉博夫斯基的实验室是招收本科生的。“一天下课后,他问我是否愿意去他实验室度过这个夏天。机会从天而降,让我大吃一惊,所以放弃了生化实验室的B计划。”
搭设备,找实习
格拉博夫斯基想开展一个光声量热计项目,旨在测量光激发的分子松弛并释放热量导致局部溶剂膨胀时形成的压力波。“把麦克风放在试管的边缘,你就可以听到声波。”研究者通过波的振幅了解以热量形式损失的能量。
贝尔托西需要构建和组装组件以测量声波,并将这些模拟信号数字化。到夏末,她又创建了一个将这些数字信号转换为图形的程序。
最后,这个项目成为了贝尔托西的本科论文。当她离开实验室时,仪器已经搭建完成——尽管她从未进行过任何实验。“这项工作不是有机合成,但它教会了我,你不必事先就很清楚通往大目标的道路——每天你做一些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杂草会慢慢被除尽,道路会变得更加清晰。你或许会被巨大的挑战吓到,但要知道问题的解决并非一蹴而就。接受超出我能力范围的项目是很棒的经历,我需要尽全力解决所有问题。”
当然,除了在物化实验室钻研设备,贝尔托西也一点没放下有机合成。她如此说道:“虽然摆弄电脑和激光很有趣,但我真的很喜欢思考有机分子的行为,也非常期待创造新分子。我对酶如何操纵分子非常着迷。”
在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暑期实习给了她更多灵感。贝尔托西与年轻的科学家克里斯托弗 · 奇德西(Christopher Chidsey)合作,研究金表面上的烷基硫醇自组装单层。“我还没有做任何合成,但至少我溶解并制备了有机化合物!我想我已经掌握了一项有用的技能!”那年夏天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的文章至今仍是她被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之一。也正是从那以后,贝尔托西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成果。
独立发论文的化学研究生
在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攻读研究生后,贝尔托西的合成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开始跟随马克 · 贝德纳尔斯基(Mark Bednarski)开展生物学研究,致力于分子设计。
贝德纳斯基是贝尔托西在哈佛认识的一位年轻学者,他当时在乔治 · 怀特塞兹(George Whitesides)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研究员,对碳水化合物化学/糖科学非常感兴趣。根据贝尔托西的介绍,那会儿他正研发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米韦来扎(Zanamivir)和奥司他韦(Oseltamivir)以作流感药物,这两种药物都与唾液酸相似。但到入学后的第三年,贝德纳尔斯基被诊断出结肠癌。他请假接受治疗,之后决定成为一名医生,并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医学。贝尔托西并没有转去其他课题组,而是在没老师监督的情况下独自完成博士学位。
她回忆道:“由于监管和安全方面的问题,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了。我回想起那段时光真的感觉有点疯狂!我心存感激,因为我的项目终于重回正轨了,我可不想去别的实验室从头再来。”
之后两年,贝尔托西和两名同组的研究生同学自主开展研究并投稿(甚至敦促编辑评论)。“当时我们有点沮丧,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回想起来,在没有PI的情况下,我们学会了更积极更高效地完成任务,解决问题。
拿到博士学位后,贝尔托西进入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免疫学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其间她再次遇到了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奇德西。后者鼓励她申请化学生物学方面的学术工作——当时斯坦福大学正寻找合适的化学生物学家。她回忆说:“我意识到自己想留在旧金山湾区,所以我也申请了UCB和UCSF。”这三所高校都给了她工作机会,而她选择回到伯克利。
贝德纳尔斯基在与结肠癌抗争了14年后,于2006年去世,享年47岁
生物正交化学的诞生
成为博士后的贝尔托西发现研究生物系统中的糖科学多么令人沮丧——研究工具是如此原始,以至于无法测量细胞、组织或器官,“我认为必须有更好的方法”。
这成为她在伯克利的第一项科研任务:开发合适的工具,帮助糖蛋白科学家更高效地取得进展。当时科学家可以借助成像技术观察蛋白质或核苷酸,但对于糖,他们还拿不出好的成像方法。鉴于此,贝尔托西开始研发成像工具,并尝试在糖上放置了探针,以便对其进行监控。这带来了一种代谢标记方法——通过代谢前体将标记物置入糖中,从而成为细胞的“食物”的一部分。她说:“探针本身不能以这种方式插入,因为它们太大,会被酶破坏,但你可以在糖上面贴好化学标签,然后再添加探针。”
贝尔托西奉上了一种新型反应,所谓的“生物正交化学”。这种化学反应发生于生物体内,但不会与任何自然生物过程相互作用或彼此干扰。她实验室的工作包括开发生物正交反应方法,以及对标记好的糖进行应用和成像。
“然后,新的想法从正进行着的项目中出现。”那时刚发布结核杆菌的基因组序列,研究生约瑟夫 · 穆戈斯(Joseph Mougos,现在已是一名成功的学者)对此充满研究热情。贝尔托西表示:“我们正研究各种人类酶,于是将它们的基因序列与结核杆菌的基因组进行比较,看能否从微生物中找到酶的 ‘远亲’。就在这个过程中,穆戈斯惊讶地发现了人类硫酸酰基(磺基)团,一种转移酶的‘远亲’,可以将硫酸酰基连接到糖上。”
下一步是制造突变体并寻找表型,但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与结核杆菌打交道需要有3个生物安全控制设施的支持,而贝尔托西的实验室难以满足条件。“我是助理教授,资金紧张,但同时我又想,如果我作为一名本科生能搭建出量热计设备,我为什么不去尝试研究结核杆菌和磺基?”之后,穆戈斯找到了必要的满足安全要求的设备,也想出了如何诱导突变。“我们开发了一个大型监管平台,使我们能够使用富含硫酸盐(其中的硫元素为硫-34)的标记物来寻找代谢物。”
贝尔托西说道:“我们发明了一种荧光标记试剂。现在这个项目得到了比尔和梅琳达 · 盖茨基金会的支持。我们希望创建出即时诊断系统。如果没有学生去推动结核病研究,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花了10年时间才蹚出这条路。”
聚糖酶与转录因子
在伯克利待了近20年后,2015年,贝尔托西再度收到了斯坦福的邀约。“这一次众星云集。他们在化学生物学领域做了大量投入,新建了一座大楼,新增了20名教职员工,其中包括几位资深教授。”斯坦福当时正建立新研究所,对她来说,这似乎是开启另一段学术征程的大好机会。
贝尔托西本没有考虑离开伯克利,而且当时的时机也不理想,因为她和爱人正准备迎接第三个孩子,但她很快确定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接受这份工作。“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在医疗生态环境中获得经验,这在伯克利并不容易,而斯坦福有一所医学院,所以我们搬到了旧金山。”
下一个意想不到的研究方向很快就出现了。“我接到斯坦福校友克里斯汀 · 威尔西(Kristen Wilsey)的电话。她如今是个成功的科技企业家,其小女儿格蕾丝被诊断出患有一种极为罕见的遗传病——她体内的Ngly1基因发生突变,导致先天性去糖基化障碍。Ngly1基因编码N - 聚糖酶1——存于细胞质基质内,负责切除错误折叠的糖蛋白中天冬酰胺连接的寡糖链。威尔西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研究基金会,旨在寻找治疗方法。他此前招募了几位知名的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鉴于我的实验室致力于糖科学研究,他想知道我们能否在其中做些工作。”
“在没有很好地理解N - 聚糖酶的丧失如何致病的情况下,我对于提出一项研究计划感到犹豫不决。”贝尔托西当时尚未就N - 聚糖酶的功能理清头绪,也给不出一个关于酶缺陷与患者症状间关联的合理假设。
加州理工学院比格特·德赛斯教授
几个月过后,巧合再次发生。在一次会议上,贝尔托西与加州理工学院的比格特 · 德赛斯(Biogart Ray Deshaies)聊起了N - 聚糖酶。实验室培养皿中的大多数经过Ngly1突变改造的细胞并没有如预期那般发生去糖基化障碍,充满糖蛋白“垃圾”,反倒是在没有N - 聚糖酶1的情况下过得很好,可是缺了N - 聚糖酶1的人类和实验室小鼠却都病得很重。
他们开始怀疑生物体的某些细胞内存在重要的底物(实验室培养出来的细胞则不一样)。一个人要想保持健康,这些糖底物必须通过N - 聚糖酶1去除——但寻找这些底物是一项重大挑战。
德赛斯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NRF1这一不同寻常的转录因子。它在调节细胞内蛋白质以及维持神经元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也能限制蛋白酶抑制剂的有效性。但根据德赛斯的理论,NRF1必须在活化状态下才有效,而其表面的一些糖分子会阻止它被激活,因此去糖基化——更准确地说,去除它表面的N-聚糖——对于NRF1的激活至关重要。
贝尔托西团队通过实验进一步发现,缺少N - 聚糖酶1使得NRF1难以活化,也就无法维持神经元和其他细胞的正常运转——这可以解释Ngly1基因缺陷患者的一部分临床表现。在利用N - 聚糖酶1完成了NRF1表面的去糖基化后,他们看到突变小鼠不再出现相关症状。
贝尔托西表示:“我们将开展更接近斯坦福临床科学目标的研究。这是一个始于患者的项目,现在成为我们实验室努力的一大方向。”
另一方面,贝尔托西也将目光投向了免疫肿瘤学。这是一个热门领域,也有糖科学研究者的用武之地——糖基化在肿瘤微环境的免疫调节方面起到重要作用。“这是糖科学家的好机会。生物学家正使用基于CRISPR的基因组筛查来寻找糖关联基因的重要作用,非常希望与那些能找出相关生化途径的专家交流合作。
“机遇引领你前进。如果你足够幸运,你会发现一些机会。更多人可能会错过很多机遇,因为我们精力和时间有限。你无法关注到每一件小事,但如果你看到了它,你一定要努力抓住它,跟着它前进。”
资料来源 Chemistry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