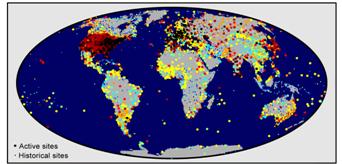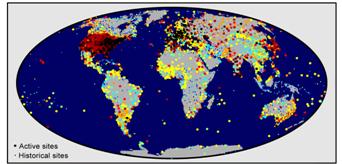新一代的精密地球模型“HadGEM2-ES”正在为其第一次“大考”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然而,其增加的复杂性是否可能会给未来的气候预测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外貌
挑战极限
在英格兰南部有一幢三层高的玻璃幕墙政府大楼,看上去既开放又漂亮。但是,戒备的警卫以及其他安全措施却时刻提醒着路人――英国国防部正在此处开展敏感且对国家未来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在这栋大楼地下室的两个相连的房间里,由27个大黑盒子组成的超级计算机,正以每小时处理100万行计算机代码的速度,以此来一窥地球以及70亿居民的未来。
这里正是英国气象局正在运行的超级计算机的“家”(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气候模型)。这一新近由英国气象局哈德利中心科学家开发完成的模型,将在未来几个月内迎来它的第一次“大考”――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于2013年公布的下一份有关气候变化物理基础的报告运行一系列的数值模拟。

HadGEM2-ES计算机模型
这一被称为“HadGEM2-ES”的模型研发耗时四年(HadGEM2-ES意为添加了地球系统的哈德利中心全球环境模型第二版),是全世界正在研发的十几个地球系统模型之一,但它已经远远超出了那些仅仅考虑了空气、阳光和水等气候物理要素的早期模型。这一新一代的模型不仅包含了上述这些要素,还囊括了更多:可以作为条件缩放的森林;能随着海洋酸性增加而变化的海洋食物链;在大气中通过与温室气体相互作用能加强或影响其变暖效力的气溶胶粒子等。
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增加的复杂性能给他们带来更切合实际的预报,并从中获得有关气候要素之间是如何互相作用的新认识。但是,不管这一惊人的尝试是否真的能帮助政治领导人和科学家来筹划地球的未来,它多少带有一点赌博的味道。由于模型中模拟了更多的元素,而这些元素难免会发生变化,额外的复杂性因此会加大对温度或降水等预报的误差,包括用于下一份IPCC报告的模型很可能会给出未来气候的多种结果。
类似描述大气环流和热力学等一系列方程组的其他气候模型,HadGEM2-ES通过求解其中许多点的值组成了一个覆盖地球表面的三维网格,其网格由均匀分布在东西和南北向的192个和144个格点构成。每个三维网格单元所覆盖的表面是经度为2°×宽纬度为1°的区域,在赤道上其对应的约为100千米×200千米的区域。其中,大气被划分成彼此不等的38层,在接近地面和海面的区域每一层厚度约为20米,但随着高度增加,厚度会逐渐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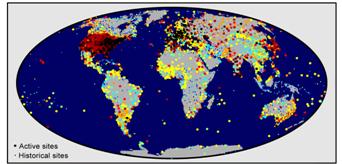
由东西向192个和南北向144个格点组成了一个覆盖地球表面的三维网格
代码取代
如同所有的现代全球气候模型,HadGEM2-ES也包含了大气模型和海洋模型的相互作用(耦合)。1980年代~90年代初,在最早的哈德利耦合模型中的海洋被称为“沼泽”,只不过是连接大陆的大型浅水塘而已。随后逐渐演变成了“板块海洋”――虽然呈刚性,但可以吸收和释放热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HadGEM2-ES中的全球海洋,具有洋流和涡流――海洋被划分成40层,深度为5000米,最顶层厚度只有10米。这一重要的突破使得模型可以更真实地模拟海洋是如何在不同深度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
在哈德利中心,科学家们冥思苦想的如何模仿云、水流、树木和冻原以及地球上其他无数可以放大或减小全球气候变暖的物质。然而在这里,这些复杂的工作被完成的唯一标志只不过是计算机电脑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例如一个封闭的碳循环,它在理论上可以解释未来几个世纪地球上对气候造成影响的所有碳。这一模型囊括了详尽的大气化学、可随着气候生长和死亡的植被以及可独立响应不断变化的温室气体水平的海洋生物和地球化学系统。
在陆地上,植被从灌木到针叶林被划分为9类――这是如何在模型中体现生物圈的一大进步。在气候模型中加入生物学的首次尝试是把所有的生命处理成一个从两极到赤道、均匀覆盖的“绿层”。作为HadGEM2-ES的前身,HadGEM1也包括了和HadGEM2-ES相同的植被,但它是静态的。现在,模型中的植被类型可以变化,树叶会随着季节性周期而改变。
把这么多元素同时融入一个模型会大大减缓它的运行速度。模拟一个月的气候需要一个小时时间。“这就是为此付出的代价,”一直致力于HadGEM2-ES研发的碳循环专家克里斯·琼斯(Chris Jones)说。而HadGEM1的运行速度是新模型的3倍。
即便有着精细的分辨率,但一些在气候上的重要过程,例如云,对于HadGEM2-ES而言还是太小无法直接模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气候模拟采用了一种被称为“参数化”的技术。例如,与试图在某个网格内模拟云不同,一系列描述云的形成和消散以及它们对辐射的吸收和反射的方程被用来描述它们对气候的影响。然后再对每个网格进行平均。
识别误差
运用参数化技术可能会引入误差。不过,更麻烦的也许是随机误差,只要输入一小点错误的数据就会使整个系统失控。哈德利中心的科学家发现,如果他们为世界上的干旱地区所设置的植物太少的话,结果就会造成没有充足的植被来固定土壤,模型大气中的尘埃水平就会上升并失去控制(3倍于平均值);反过来又会影响海洋,导致浮游生物疯长。
为了确定这些误差,每个模型都要经受严格的测试,包括对模型进行一系列的“控制运行”,即通过模拟一个稳定气候来对其进行测试。此外,还对过去的气候进行模拟,以此判定它再现历史气候变化的能力。目前,HadGEM2-ES正处在这一测试阶段。
当结果与现实不吻合的时候,研发人员会利用他们对气候系统的认识来识别模型中可能的误差并进行修正。但这偶尔也会导致对问题的新的认识。例如,在HadGEM2-ES中与现实不符的沙尘暴却揭示出,即使是沙漠中的少量植物也会影响全球的气候。
尽管在测试阶段通常会把模型调整到能模拟过去和现在的气候,但往往也会造成一些问题。事实上,每一个模型都有弱点。当哈德利中心研发HadGEM1的时候,这个模型就很难模拟“厄尔尼诺”南方振荡现象――它会驱动许多横跨太平洋的气候变化。(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科学家使用的模型在“厄尔尼诺”身上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美国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的气候学家罗纳德·斯托弗(Ronald Stouffer)则说,在上一份IPCC的评估报告中,他们的模型在模拟北太平洋海冰上是“世界上最差的”。

对冻原地区的环境预测,“HadGEM2-ES”是根据代码识别的
不过,当这些模型被用于再现全球范围内过去和现在的气候时,它们却是最好的。“这正是我们这一行的乐趣所在,”斯托弗笑着说,“你可以让你的模型整体上表现出色,但在某一点上却可能会极为糟糕。”在接下去的几个月为IPCC进行模拟之后,HadGEM2-ES的盲点应该也会显现出来。
不管HadGEM2-ES可能存在什么样的不足,都有可能被其他的模型弥补,包括来自GFDL、NCAR,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日本和挪威研究小组的模型。“模型的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气候建模专家安德鲁·韦弗(Andrew Weaver)说。因为当涉及到建模的过程中,“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方式”。同时拥有多个模型的优势是,它们进行模拟的方式都各不相同。
“这些模拟中的每一个都是一项挑战,直到最后一刻我们才会知道一切是否能按照我们预期的进行,”在德国马普气象研究所领导植被建模的克里斯蒂安·赖克(Christian Reick)说。由于许多小组拥有一系列不同等级的模型,如果地球系统模型对温度的变化预测具有不合理的、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则可以回到更为熟悉的模型来对未来的气候进行更为简单的模拟。
实际限制
由于模型的复杂性在不断增加,这使得有人开始呼吁必须谨慎从事。“你必须偶尔停下来想一想,这些复杂性是不是正恰恰说明了我们的无知,”GFDL现代气候模型奠基人之一的真锅淑郎说,“但你又不想过于简单化。”他补充说,关键是“模型中的细节是否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相平衡”。
虽然从学术的角度来看,新的模型正在日臻完善,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它们却并不一定能产生更为有用的结果。琼斯承认,只有当我们对模型的了解达到了可信赖的程度,它们才是有用的。“我们正在进入无法用观测来限制的未来,气候模型是我们唯一可用来预测的工具。”
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IPCC的作者会分析所有模型的预测,以此对未来的气候进行最佳的估计。这将包括温度的上升将有多快、哪里的降雨量会增加或减少、植被将发生如何的变化。
不过,即便IPCC使用最新的模型来进行气候模拟,但琼斯和他的同事仍然在思考如何对它们进行完善,其中之一就是,融化的北极冻土会通过释放甲烷――一种有效的温室气体――来加速变暖过程。HadGEM2-ES已经考虑了来自湿地的甲烷释放,但没有考虑冻土层的。另外,哈德利中心的下一个模型将会包括氮循环以及它对植物生长的影响。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纯碎为了研发出一个完美的模型”,一气候建模专家说,“我们会根据对系统的最佳认识来研发新的内容,当我们对这些过程有了信心之后,就会把它们放到模型中去。”
对于气候学家来说,模型不仅仅是能一窥未来的工具,它还是一个试验场――一个可用来检验他们对气候系统认识的“地球副本。”对于没有能力在实验室或者野外进行全球规模实验的人来说,模型是他们拥有的唯一工具。
在哈德利中心,一些工作人员开玩笑地说,模型研发人员最终将尝试把大熊猫也放到他们的模拟中去。或许他们也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模型永远也不能完全代表真实。“我们面对的挑战之一就是要找出对于模型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琼斯说,“永远都会有一些细节或复杂性是我们无法囊括的。”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