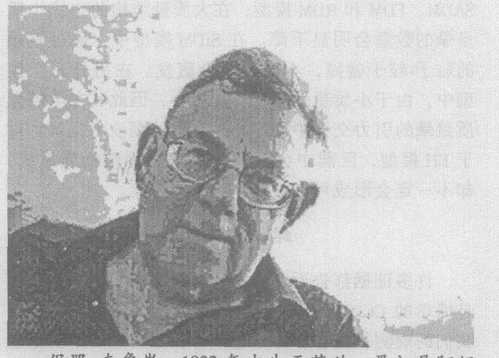因成功揭示南极臭氧空洞咸因而获诺贝尔奖的荷兰科学家保罗 · 克鲁岑,在科学上还有多项重要贡献;是他首先意识到热带森林燃烧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之一,也是他率先发出了核冬天的警报。而在此之前,又是他和他的同事首先开创了数字天气预报模型。在以下对《新科学家》杂志记者的访谈中,保罗 · 克鲁岑回顾了自己如何从一个没有多少研究背景的工程师到成为一名在大气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的经历。在看似随意的交谈中,克鲁岑还是透露了不少在科学上如何做出原创性工作的心得,如敢于质疑,不放过任何事物;不仅仅停留在观察的表面,喜欢实干等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克鲁岑在事关名誉、名声问题上表现出的大度和宽容,这似乎使他失去了不少应有的辉煌和名声,但最终却赢得了更多人的尊敬。
保罗 · 克鲁岑,1933年出生于荷兰,最初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桥梁工程师,随后他改行研究大气科学,继而成为臭氧层及其他大气化学领域的先驱学者。他先后发表了350余篇学术论文,参与撰写或编辑了8部著述。目前,他同时在德国美因兹的马克斯 · 普朗克化学研究所和美国加州的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
记者:您的科学生涯无疑是丰富多彩的,请问它是怎样开始的呢?
克鲁岑:我在科学领域的起步较晚。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我因为一场由接种天花疫苗引起的高烧错过了去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考试。于是我上了一所工程学校,经过4年的学习并服满兵役后,我在阿姆斯特丹开始了桥梁建筑师的工作。但因为酷爱冬季运动,后来就和我妻子移居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天我看到了一则斯德哥尔摩大学气象学院招聘电脑程序设计员的广告,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我还是得到了那个工作。
记者:这在当时是一项前沿性的工作,不是吗?
克鲁岑:我想是的。我能够用上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脑和最早的数字天气预报模型。那时,所有的机器语言都得由我们自己设定,我还记得和工程师们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仔细听着计算机发出的声音,来判断它们是否工作正常。
记者:这对一个26岁、没有大学文凭的桥梁建筑师来说算是不错的了。但您的目标显然更高。这以后又过了多久您开始思考关于臭氧层的问题?
克鲁岑:气象预报的工作吸引了许多美国科学家。1965年,也就是32岁时,我受邀协助他们中的一位建立一个臭氧层的电脑模型。当时的模型简单极了,牵涉到的反应很少。这时我开始阅读相关文献,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总觉得臭氧层理论有些地方不太对劲。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化学物质和反应来完善理论。
我想这其中应该包括氮氧化物,但我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公开发表我的想法。我没有数据。当时还没人知道大气中有没有氨氧化物。即便那时我已经37岁,而且还获得了数学学位,我依旧认为科学家就应当是爱因斯坦式的人物,而绝非我等之辈。但最终我的论文还是在1970年发表了。
记者:不久以后,人们就开始担心协和之类的超音速飞机对平流层造成的危害.....
克鲁岑:是的,而且我的论文使我成为了第一个意识到它们排放的氮氧化物会对臭氧层形成危害的人。那时候我紧张极了,作为一个毫无化学背景的人,我居然撞上了这样一块烫手山芋。没办法,我只能靠自学了。由于我当时所在的牛津地区邮政工人罢工,耽搁了我论文的修订工作,最后哈罗德 · 约翰斯顿反而在我之前第一个发表了论文。
记者:您当时一定失望极了.....
克鲁岑:嗯,实际上我很高兴看到有这样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支持我的观点。幸好从此以后超音速飞机再也没有大量生产了。此后不久,我的兴趣又转向了氯化物对于平流层的影响。
当时有一篇马里奧 · 莫利纳和雪利 · 劳兰撰写的著名论文。我读后起先感到很失望,因为当时我也在考虑氯化物的问题。只是我此前还不知道氯氟烃是氯的一个来源。1974年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会议上我报告了他们的这一发现。当时有个记者在场,此后关于氯氟烃的事就变得妇孺皆知了。
我做了平流层中氯元素存在形式的第一个模型,并计算出在某一高度它能破坏40%的臭氧层。我猜想那可能是个挺重要的贡献。最后到了1995年,我们三人因为这项工作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
记者:这其中是不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您几乎被人遗忘,而劳兰和莫利纳则声名鹊起?
克鲁岑:可能是吧。但10年后,也就是80年代中期,我参与发现了南极上空臭氧层空洞的成因。结果终于还是牵涉到了氮氧化物,因为氯氟烃必须依附于硝酸溶液的冰滴来破坏臭氧层。这个结论也为后来禁止氯氟烃(氟利昂)的《蒙特利尔公约》铺就了道路。
记者:后来您就提出了关于核冬天的想法是吗?
克鲁岑:是的,那是我的想法。当时人们很担心一场核战争将会对臭氧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1981年,一家杂志社约我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一开始我拒绝了。当时我错误地认为,原子弹都足够把我们杀死十次了,干嘛还要担心以后的环境污染呢?但主编坚持要我写。
有一天,当我和同事约翰 · 布克一起时,我们突然想到,在一场核战中,你到处都能看见火,于是就会有很多烟灰散布在大气中,使得白昼像黑夜一样昏暗,因此温度将会骤然下降。这些的确都是很简单的推论,但在科学中,思路正确是最关键的。不管怎样,那成了一条大新闻。这对军事产生了很多影响,它使我更坚定地相信,我们必须禁止核武器。
记者:然而,您又一次没有得到应属于您的荣誉。美国科学家卡尔 · 萨根利用您的想法成为了新闻人物......
克鲁岑:对,你说对了一部分。正因为核冬天的问题太重要,所以我个人的得失倒无所谓了。其次也是因为萨根的交际能力太强,但我不介意。他也总是承认我们的贡献。我从未对这件事怀恨在心。我对其他种类的火也非常感兴趣,比如森林大火和热带地区庄稼废料所引起的火。1980年我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提到,全球有如此众多的生物正在不断燃烧,它们才是全球大气污染的主要肇事者,燃烧过程中产生的许多非常活泼的化学物质都值得我们好好研究。
后来我又渐渐了解到,这些大火形成的烟雾气溶胶对气候的影响力毫不逊色于温室气体。但我们还必须实地观察。20世纪90年代初期,拉玛纳森和我提议去调查一团来自印度并正在向印度洋扩散的巨大云雾。1999年,提议最终成为了现实,我们调集了200余位科学家、3艘船只和几个地面平台分别采集空气样本。不论是直接观察还是改变云雾的光学性质,我们都发现,这些云雾至少阻挡了10%以上的太阳能,并且在很多地方早已抵消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事实上从全球角度看,生物的燃烧抵得上全球变暖影响的四分之三。而气候学家们还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记者:这样说来,穷国造成的污染因为能和富国制造的温室气体相抵消而拯球了地球?
克鲁岑:到目前为止,是的。但问题在于,多数气熔胶只能在大气中存在几天罢了。而温室气体的寿命有一个世纪或更长。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气溶胶将逐渐败下阵来,因而无法保护地球免受温室气体的毒害。
记者:您为人类对大气层的无知而感到担忧吗?
克鲁岑:当然。当我们像现在这样对地球的自然进程进行大规模干预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将造成的危害的无知是令人震惊的。人类永远不应该忘记在臭氧层问题上我们有多么幸运。假如20世纪80年代英国南极考察队的乔 · 法尔曼及其同事遵守了,上级的命令,而没有坚持考察南极上空臭氧层的话,我们也许还要等到臭氧层空洞已经蔓延到南极洲以外的某个人口稠密地区时才能注意到它。
再追溯得久远些,更让人感到庆幸的是,上世纪初制造喷雾器和冰箱的工业家们选择了氯的化合物,而不是性质极其相似的溴。假如他们当初用的是溴,那么只需到1970年,灾难性的臭氧层空洞将遍布于世界任何角落的上空,而且一年四季都难逃其魔掌。
记者:您曾说过中纬度地区可以置身事外。这又是为什么呢?
克鲁岑:这话固然有点争议,但我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地球的重大变化总是要么发生在热带地区,要么发生在高纬地区。热带地区的高温给大气中的许多化学反应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而在两极附近,除了臭氧层空洞以外,还发生着许多能加速气候变化的自然反馈:比如冰和永久冻结带的融化,还有洋流的变化等等。永久冻结带的融化会释放出大量的甲烷,它的温室效应要远远强于二氧化碳,是极其危险的。
记者:您的最新发现似乎更像是一项发明:名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地质学新纪元。
克鲁岑:那是在3年前的一次会议上,有个人提到了“全新世”,也就是从最后一次冰期(即第四纪冰期)末至今的这段地质时期。我突然觉得这种说法错了。在过去的200年中,人类已经成为了主导的地质学因素。所以我当时就说,不,我们已不再处于全新世了,而应该叫作“人类世”。这个名词是我当时即兴造出来的,现在看来已经被人们接受了。
记者:假如您现在要在大气化学领域白手起家,您会选择什么方向呢?
克鲁岑:我很幸运。我当初起步时,只需要了解4个化学反应。现在你得知道几百个。尽管大气化学是如此美丽,但如果你现在还是个新手,就会觉得很复杂。要是我的话,也许我就懒得碰它喽。
记者:您做学问似乎向来很大胆。当您有一个好的想法时,即使没有数据资料,您也会想办法去实现。还有,您不乐意和大部队一起干,有什么原因吗?
克鲁岑:这可能和工程师的职业有关。我不会仅仅停留在观察的层面上,我喜欢实干。也可能和我是个气象学家有关。天气变化是非常混乱的,于是在试图预测天气的过程中我意识到,即使有了计算机的帮助,直觉还是必不可少的。我还学会了质疑,不放过任何事物。所以每当一篇学术论文中写着“众所周知......”时,我就告诉自己没准儿里面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
记者:这种态度也许是您的基因决定的吧?
克鲁岑:不知道。我父亲是个酒店招待,母亲在医院食堂工作。他们都是善良的人,但不搞学术。我有个叔叔棋下得很棒,对天文学也很有兴趣。但他是个煤矿工人,根本不可能有搞科研的机会。儿童时期我看了很多关于探索的书籍。那时正值战乱,我们哪儿也去不得。所以我当时只看到过平原,山峰也只能出现在想象之中。我曾经看到积云的顶部,却以为那是积雪的山顶。这样的错觉但愿以后不会有了吧。
[New Scientist,200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