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斯德研究所是巴斯德战胜狂犬病的产物;因为接种抗狂犬病疫苗恰恰代表了世人之所需——
科学伟人首先是一个有能力在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时适时地识别问题的所在者,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周围那些有天赋的同事者——能够在学生中发现那些具备必要品质来继承自己并发展自己提出的理论或所创设的学科者。
巴斯德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在创建了一门新的科学和医学并在自己周围凝聚了一批同样充满激情的有天赋的研究人员之后,成功地把他的科学家同行置于一个专为能让他们探究他的思想而设计的工作环境之中。巴斯德研究所专为用巴斯德及其助手们研制的方法“治疗被咬所致的狂犬病”而设立,并得到公众的捐助而得以建造起来。可谓人人参与,个个捐助。捐赠者来自各个国家,不论贫富,有诺曼底集镇上的邮递员也有俄国沙皇;有侏罗纪公园的警察也有巴西皇帝;有匿名的偷猎者、《先驱论坛报》社社长还有孟加拉骑兵团。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巴斯德研究所的落成典礼也许颇为张扬,但早期的经营确实是相当寒酸的。仅有一幢房子,既用于疫苗治疗又用于研究工作,同时又是巴斯德及其家人的住所。研究所有五个所谓的“微生物”部门。有五位学科、个性完全不同的科学家聚集在大师的周围;他们是著名的化学家埃米尔 · 迪克洛(Emile Duclaux)、物理学教授尚贝朗(Chamberland)、医学博士格朗谢(Grancher)、伊利 · 梅奇尼科夫(Elie Metchnikoff)和虔诚追随大师的学生埃米尔 · 鲁(Emile Roux)博士。鲁博士对梅奇尼科夫是这样描述的:“这位45岁的来自欧洲中心的人,有一张热情洋溢的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头蓬松凌乱的头发,绝对具有那种科学天才的气质。”
在巴斯德之后,研究所由埃米尔 · 迪克洛负责管理;在迪克洛之后,则由埃米尔 · 鲁负责管理。由于他们是与创始人最接近的两位同事,因此研究所的管理仍保持了巴斯德的领导风格。鲁是一位严厉的人物,一位世俗的圣人,他通过给研究所蒙上一种等级感、一种冷漠的军营气息强化了这种领导风格。
鲁没有家庭,由巴斯德医院的护士负责照料。在他的眼里,隶属于巴斯德之家这样的荣誉是无法以价格计算的,那就是他为什么认为适中的工资是理所当然的原因。这种以鲁先生为代表的近乎修道士式的虔诚不但长期以来,而且常常仍被视为典型的“巴斯德人”(Pastorian)特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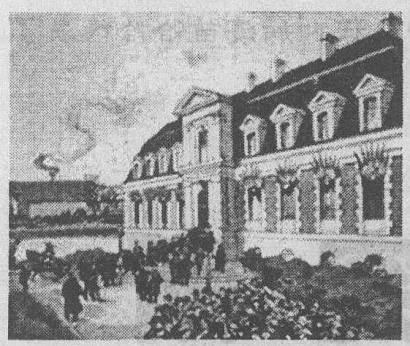
巴斯德研究所落成典礼于1888年11月14日举行
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历史上,众多名字与发现联系在一起,描绘着生物学的发展以及人类与重大灾难所作的斗争:例如鼠疫与耶尔森(Yersin);疟疾与拉韦朗(Laveran);斑疹伤寒与尼科尔(Nicolle);白喉与鲁(Roux)和拉蒙(Ramon);结核病与卡尔梅特(Calmette)和盖兰(Guerin);某些防御机制的发现与博尔代(Bordet)和后来的乌丹(Oudin);噬菌体与德埃雷尔(d’Herelle);磺胺类药物与特雷福埃尔夫妇(Trëfouels)、尼蒂(Nitti)和博韦(Bovet)。
自创立以来,巴斯德研究所以其与众不同的特色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研究和教学团体。首先是它独特的科学家群体。巴斯德以他第一次选择的同事培育出新型的研究者一一“巴斯德人”(Pastorian),他们是从世界各地招募来的,如伊利 · 梅奇尼科夫。典型的巴斯德人要么有科学背景,要么有医学背景,他们长期位于官方机构和官方职业的外围。巴斯德人是没有专业的医生、没有药房的药剂师、没有产业的化学家、没有席位的大学教师,其地位只由他的风格,首先是由他的工作单位所决定——他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以其科学背景和人才的多样性,大家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从众多不同的角度研究同样的材料,巴斯德研究所早在“跨学科研究”这一术语出现之前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学科研究”中心了。虽然后来巴斯德人获得了某种地位,但巴斯德研究所仍保持着它的多样性,即由不同背景的研究人员所组成,包括许多在外国接受培训的人员。
研究与应用密切相结合是巴斯德研究所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也许没有人比巴斯德更懂得如何科学的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巴斯德把这种统一结合进了他的研究所的组织机构之中;研究把点子提供给产业,产业反过来为研究提供资金。如果巴斯德研究所没有成为领先的欧洲生物产业中心,那么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巴斯德人自身在商业和产业方面表现出很少的天赋或兴趣。然而,那也是由于私人产业几乎没给他们多少支持这一事实,因此巴斯德研究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财政困难。在那以前,巴斯德研究所一直依靠自己的资源生存下来。
1974年,管理机构高屋建瓴,准予巴斯德研究所相当于一半预算的年度补贴,虽然巴斯德研究所保持着它作为私立基金会的地位。同时,在时任研究所所长的雅克 · 莫诺的鼓动下,生产与研究相分离,至今仍与两家大型制药康采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以此方式保持它作为私立基金会的地位,尤其是由于若干捐赠和遗产,巴斯德研究所得以保持它的灵活性和它对研究中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反应能力,对于公立团体来说,这些往往是无法做到的事情。
巴斯德研究所最后一个与众不同的特色是它向全世界扩展的能力。因为巴斯德之家的历史不仅仅只是一长串发现,也不仅仅只是那些乏味地、耐心地参与此项工作并使研究所成为今天这样规模的研究者或工程师、助手或技术员、工人或实验员们的一串名字,无论出名与否;而且也有那些在巴斯德研究所获得培训后走向世界各地去实地研究完全不同种疾病的科学家们,以及在现场建立按他们在巴黎所学原则运行的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
事实上,巴斯德扩展了他在海外的活动领地。他派遣他的第一批学生之一、年轻的军医阿尔贝 · 卡尔梅特(Albert Calmette)到远东与狂犬病和天花作斗争。卡尔梅特在越南西贡建立起实验室用以制备疫苗。被咬和潜伏着狂犬病患者从四面八方——从暹罗(泰国的旧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新加坡、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甚至日本——蜂拥而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卡尔梅特就接种了将近500,000人。
西贡的分支机构只是巴斯德研究所整个海外星团的其中一员。从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到卡宴(法属圭亚那首府),从南亚到非洲大陆和地中海沿岸,众多研究分所始终保持着与总部的联系,尽管有政治上的考验和磨难。由于有了这些分支机构,巴斯德人始终得以并且依然能够对热带疾病进行直接的研究。
巴斯德的方法始终以同样的精神、同样肯定的判断力应用于海外的研究分所。拿亚历山大 · 耶尔森(Alexandre Yersin)为例。耶尔森来自瑞士,他年轻时到巴黎学医,不久就开始与巴斯德小组一起工作(起先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后来研究所竣工后到研究所)。作为鲁的助手,他与后者一起研究白喉,证明了“毒性物质”——即最早为人所知的毒素——的存在及其作用。然而,这位孤独的人渴望出海旅行。因此他应聘成为法国邮船公司一艘邮船上的医生,随船游历了整个印度支那。
在那段时期,中国和印度支那爆发了一场瘟疫流行病。法国政府指示耶尔森这位前巴斯德人前往该疾病流行地区研究这场瘟疫并找到医治的方案。耶尔森在香港一间竹子盖的茅屋里着手工作,当时处境十分艰难,因为英国当局方面缺乏善意,又有来自一个日本微生物学家小组的敌意的竞争。但耶尔森在几天时间内就战胜了日本竞争对手,分离出瘟疫病菌并揭示了老鼠在这场瘟疫流行中扮演的角色。
回到法国和巴斯德研究所后,耶尔森制备了一种保护兔子和老鼠的抗瘟疫血清。然后他又返回中国,因为流行病正在那儿肆虐。也就是在那儿,在一名遭受病痛严重折磨、已经衰竭并且发着高烧的年轻华人身上进行了第一次人体试验。在耶尔森为他接种之后数小时,奇迹出现了,高烧退了,病人能够安睡了,疾病治愈了。这一巨大成功的意义不亚于十年前巴斯德治愈狂犬病。
当机会来临时,巴斯德人便毫不犹豫地跨过了严格的传染病界线。在卡尔梅特第一次使命期间建立的西贡研究所进行了针对蛇毒的首次研究。卡尔梅特对这个课题如是说:“在1891年10月间的雨季,位于交趾支那(印度支那南部一个地区)南部的北莲村遭到一群叫做Capel Cobra(扁颈眼镜蛇)的有毒爬行动物的攻击,这些爬虫径直钻进当地人的茅屋,咬了四个人,结果这些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都一命呜呼了。一位安南(越南东部一地区的旧称)地区的职业‘耍蛇者’捕捉到19条这种眼镜蛇并把它们关在木桶里。地方当局决定求助于西贡的巴斯德研究所,在那儿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即这是一个重新开始对样本进行研究的极好机会,在这样的研究中有着继埃米尔 · 鲁和贝林(Behring)有关毒素和抗毒素的发现之后的浓厚兴趣。这一研究后来产生了抗蛇毒血清疗法,它对巴斯德研究所今天在进行的某些研究仍有着一定的影响。
巴斯德的工作把自列文虎克(Leeuwenhoek)发现以来一直封锁在那儿的微生物从聚居区带了出来。微生物的世界最终发现自己的位置原来是在生物界的中心。而且,在几年时间之内,人类惊讶地认识到,要是没有微生物,世界根本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然而,由于微生物很小,缺乏组织和特定习性,它们始终保持着独立于其他生物体的地位。而且,作为病原体的重要性在大自然要素变换循环中的功能,以及在某些工业中的角色等原因,长期以来使得微生物的特性没能得到合理的研究。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最终把他们的研究注意力集中在微生物学上并把它与其他生物体的研究联系在一起。
又是巴斯德人再一次提出了最有力的论据来论证生物界的统一性。通过研究细菌的营养,安德烈 · 罗夫分析了生长因素的作用,即某些细菌繁殖所需要的那些化合物,就像维生素对于哺乳动物的生长和健康是必需的一样。罗夫证明那些只为某些生物体所要求的生长因素实际上是所有生物体的构成要素;它们对于所有生命都是必需的。如果某些生物体在它们的食物中要求这些要素,而其他的生物体则不要求,那只是因为后者本身能生产这些化合物,而前者不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它表明同样的组织结构和同样的功能可以在所有生物身上被发现;整个生物界是由同样的材料构成的。几年之后,遗传学工作者在罗夫的观点基础上重新开始对微生物的营养进行分析。生化遗传学就这样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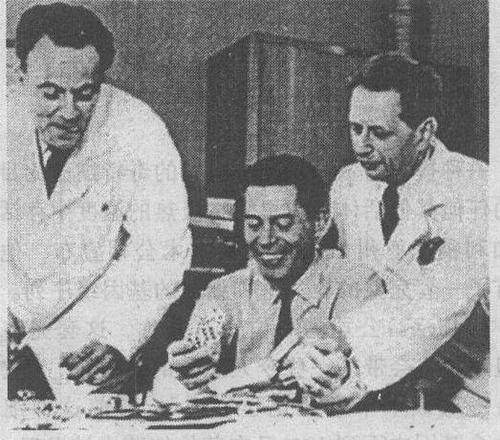
自左至右: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1920-)雅克·莫诺(Jacques Monod,1910~1976)和安德烈 · 罗夫(Andre Lwoff,1902~1994)
自那以后,形势发生逆转。细菌非但不再与其他生物体相远离,而且成为细胞及其功能和合成的研究中所选用的材料。圆圈就这样闭合起来了。巴斯德的历程把他从结晶学和酒石酸分子带到生物界和微生物。分子生物学正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并且以细菌作为出发点研究构成生物体的主要分子的结构和功能。在分子生物学(它将在几年后改变我们对生物界的观念并渗透到生物学和医学的不同领域)的发展中,巴斯德人一一如安德烈 · 罗夫、雅克 · 莫诺、弗朗索瓦 · 雅各布、埃利 · 沃尔曼(Elie Wollman)、弗朗索瓦 · 格罗(Francois Gros)和让-皮埃尔 · 尚戈(Jean-Pierre Changeux)等人带领的小组——将担任重要的角色。这样,在发现狂犬病疫苗一个世纪之后,蒙塔涅(Montagnier)、巴雷-西努锡(Barré-Sinoussi)和谢尔曼(Chermann)又一次在巴斯德研究所分离并鉴别出该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灾难之一负责的HIV病毒。
经历了自创建以来的100多年时光之后,巴斯德研究所今天已拥有500多名研究人员和600名学员。它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在公共卫生领域拥有9个研究部门和70个单位。巴斯德考虑大的规模无疑是正确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为196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本文首次发表于1998年4月6日,最近修改于2002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