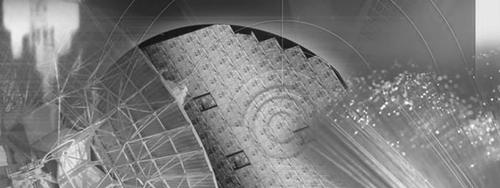
去年秋天,有一个工程学校请我去帮助他们的学生学习怎样写作,他们把我安排在物理系一间闲置的房间供我作办公室之用。从我的办公室走到楼下大厅,就会看到一幅宣传“2005世界物理年”的海报。在海报上,留着一头触电式头发的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的肖像格外引人注目。这幅海报是为纪念100年前的那个物理“奇迹年”而张贴的。那一年,一位年轻的瑞士伯尔尼专利局职员发表了5篇关于相对论、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的论文而使物理学发生了革命。这幅海报呼吁:“让2005年变成另一个奇迹年吧!”
2005年悄然已过,人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奇迹发生。这幅海报就像一张克里/爱德华兹(2004年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副总统竞选人——译者注)的保险杆贴纸一样,给人的感觉越来越不好受。走到一间开着门的物理学教授的办公室前,我向房间里的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究竟会不会有另一个爱因斯坦?这也是那幅海报以及其他纪念爱因斯坦活动背后所提出的问题。这位物理学家耸耸肩十分明智地回答:“我不清楚那问题到底有什么意义。”
让我设法说得更准确一些:爱因斯坦无疑是有史以来最著名、最受爱戴的科学家。我们敬仰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科学天才,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位道德甚至精神上的圣贤。从庄严的“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瘸子,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到顽皮的“引力不能归咎于恋爱中的人”,他的那些不朽的格言触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目前,市面上大约有500多本关于爱因斯坦的书籍在销售,其中至少有十几本是在去年出版的。这些书的作者们似乎时常在竞相滥用赞美言词。爱因斯坦的好朋友和传记作者亚伯拉罕 · 佩斯(Abraham Pais)称他为“20世纪的超人。”在《恋爱中的爱因斯坦》的作者丹尼斯 · 奥弗比(Dennis Overbye)看来,他是“面对无知的人类”的“偶像”。在《等式中的上帝》一书中,科里 · 鲍威尔(Corey Powell)拥戴爱因斯坦为进行基于理性的“科学/宗教”启示这一神圣征途中的“先知”。
因此,要重述我原来的问题:还会出现另一个爱因斯坦吗?我持怀疑态度。这不是因为我怀疑现代的物理学家在聪明才智上比不过爱因斯坦。詹姆斯 · 格雷克(James Gleick)在他1992年出版的物理学家理查德 · 费曼(Richard Feynman)的传记《天才》中曾仔细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物理学没有造就出更多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来呢?格雷克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现在还活着的有才气的物理学家太多了,以致于从中脱颖而出变得越来越困难。换句话说,我们对爱因斯坦的理解就跟看人的高矮胖瘦一样是相对的。
格雷克的解释在我看来是很有道理的。仅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理论物理学家爱德华 · 威滕(Edward Witten)就被公认为不仅是自爱因斯坦以来、而且是牛顿以来最具数学天赋的物理学家。然而,我还会附加一个推论:爱因斯坦看起来比所有现代物理学家都要伟大的原因是物理学变得渺小了。对于上个世纪上半叶而言,物理学不仅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界的理解(这些与毕加索、乔伊斯和弗洛伊德等幻想狂人的那些令人迷惑的作品相映成趣),而且还导致了像原子弹、核能、雷达、激光、晶体管以及所有计算机和通信行业里的小玩意那样的震撼历史的技术的产生。物理学至关重要。

而今天,政府投入到物理学研究上的经费停滞不前,攻读博士的美国人的数量陷入了自1960年代早期以来的最低谷。特别是像斯蒂芬 · 霍金(Stephen Hawking)所著的《时间简史》和布赖恩 · 格林(Brian Greene)的《优雅的宇宙》等畅销书所描绘的那样,物理学如果不是全然脱离了现实,就是变得越来越深奥了。许多最优秀的物理学家都为完成一项把爱因斯坦晚年所耗尽的任务所困扰,这就是找到一个融合量子物理和广义相对论的“统一理论”。而量子物理和广义相对论就像格子花纹和圆点花纹的布料一样在观念上和数学上都是不协调的。但是这种“万物之理论”的追求者们却已经稀里糊涂地走进了更高维的迷幻境地,与现实几乎甚至完全没有经验上的联系。物理学家劳伦斯 · 克劳斯(Lawrence Krauss)认为,那种不管有没有根据就对多维空间理论深信不疑的态度,是受到科学“仅仅是另一种类型的宗教而已”的思想的怂恿。
近年来,生物学已经取代物理学成为最具有智力、实用和经济影响力的学科。生物学为我们带来了诸如基因工程、干细胞和克隆这样的许多令人震撼的技术。我们最急待解决的许多问题也是关于生物学的:艾滋病以及其他传染疾病、人口过剩、物种消失,甚至战争(如果你相信进化心理学家的关于侵略的遗传起源的论述)。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自然不是向物理学家而是向具有生物学基础的科学家寻找答案。
在所有的生物学家中,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卒于2004年,原先是学物理的)可能是最接近爱因斯坦的人。1953年,克里克与詹姆斯 · 沃森(James Watson)一起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此后,他继续研究双螺旋是怎样传递遗传密码的。正如爱因斯坦徒劳地追求物理学的统一理论一样,克里克在晚年孜孜追求的是意识的神经生物学理论,这一或许是生物学中最深奥最难解的未决问题。人工智能大师罗德尼 · 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在他的著作《肉体与机器》中写道,“我们或许需要好几个爱因斯坦”来解决这一问题。
但是克里克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现代生物学家也都没有赢得爱因斯坦那样的超越科学的声望。爱因斯坦利用他的名望在演讲、评论、会见、请愿书和给世界各国领导人的书信中发表他对核武器、核能、军国主义以及其他重大问题的看法(他说的话人们愿意听)。在1952年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化学家哈依姆 · 魏茨曼(Chaim Weizmann)逝世之后,以色列内阁曾请他担任总统。出于他对和平主义和一个超国家政府的公开承诺,爱因斯坦谢绝了邀请。或许这也是对以色列各级官员的一种安慰吧(据说,在等待爱因斯坦的回音期间,以色列总理大卫 · 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曾对一名助手问道:“如果他接受了邀请,我们打算做什么呢?”)。
一位当代科学家,不论是物理学家还是生物学家,像这样受到他人的拥戴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原因可能是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失去了它的道德光环。现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清楚科技进步的消极方面,不论是核能还是基因重组。而且,因为科学已经日益机构化,人们已经感觉到它只不过是另一个追求其自身利益而置真理和公共利益于不顾的行会而已。但另一个原因是爱因斯坦拥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品质,就像核物理的黑天使罗伯特 · 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所描述的那样,那是“一种奇妙的顽固倔强的同时又不乏天真烂漫的纯洁气质”。而正是这种品质让他的一生都那么令人瞩目。
物理学家约翰 · 斯塔克尔(John Stachel)是《爱因斯坦的奇迹年》重新发行版的编者,他坚决抵制那种认为再也没有科学家能够重新像爱因斯坦那样唤起我们的敬仰的想法。最近,斯塔克尔对我说:“我希望并且相信,尽管集技术、哲学,当然还有道德于一身的天才极其罕见,但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在我的工作中所遇到的许多还处于成长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让我相信,科学的未来是一片光明。但我仍然怀疑我们是否能够碰到一个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因为爱因斯坦是时间和气质这一独一无二的方式相结合的产物。此外,爱因斯坦也不认为他自己是名副其实的爱因斯坦。他曾经说过:“我不是爱因斯坦。”当然,如此谦虚只会让我们对他更加敬仰,更加怀念。
[本文作者约翰·霍根(John Horgan)是史蒂文斯工学院科学写作中心负责人,著有《科学的终结》和《理性神秘主义》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