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发展和面临的挑战

在北京一家新落成的工业园区内,许多身着白大褂的工人正在机器旁忙碌着,通过油润的装配线把生产出的样品相互传递。这家工厂生产的既不是电视机也不是服饰,而是一天5000万单位的基因序列。它是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一个下属单位。该所产业化规模的排序作业在国际人类基因组项目中举足轻重,使中国成为参与该项目研究的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
现今,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了制造业后正在繁荣壮大,但是中国政府希望从高科技以及知识产业中获得更大的进步。因此,在1996年至2000年间,中央政府将15亿元人民币(约合1.8亿美元)投入了生物工程,作为启动这一领域的一个主要步骤。在2000年至2005年间,中央政府还计划再投资50亿元人民币。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小组估算,中国的生物工程产业将主要在京沪深三地的300个由公共投资的实验室和大约50家新兴公司中开花结果(在中国生命科学领域内工作的有2万名研究人员)。
相对于美国2001年投入生物产业开发和研究的经费以及雇用了19.1万人的规模而言,15亿元人民币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然而,中国这一产业的发展速度已使外部世界感到吃惊和不安。有人担心由于对生物工程缺乏广泛的论证,也因东西方不同的哲学传统,中国的发展可能意味着有悖于西方的道德观念。
面对这样的论断,那些工作在生物工程第一线的研究人员的心情喜忧参半。这是因为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受制于一些逆向力量,其中包括现代知识产业基础的薄弱,尤其是有关转基因作物的法规时时变化。如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所见的那样,也是中国现时技术发展中的常见现象。中国生物工程产业要想赶超欧美同行,必须战胜这些拦路虎,不过恐怕也得花上很长时间。
制约发展的因素
当你步入北京任何一家高档医院的药房间,你便会看到很多生物工程的成果,诸如由基因工程合成的治疗糖尿病胰岛素或是治疗癌症的阿尔法干扰素。事实上,现在大约有20种基因工程类药品被准许销售,其销售额在2000年达到相当可观的76亿元人民币。虽然这些都是中国生产的,但是这些产品充其量是富国发明的翻版,都是在中国对知识产权不太重视的情况下引进的。
在1966年和1967年间,中国的“文革”几乎把所有的创造发明一扫而光。国家生物工程发展中心主任王洪广(音)承认,对中国许多科学家来说,独创性仍然是一个问题,他希望现在国外的约2万名科研工作者中的部分回国人员能点燃创新之火,2002年11月,北京宣布了一项计划,承诺以西方薪金模式从国外吸纳200名科学家回国工作。
在中国生物工程领域内,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亮点,这些亮点经常体现在归国科学家的身上。杨焕明(音)就是其中一例。在1999年他回国启动并领导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前曾在欧美接受训练。该所除在人类基因组测序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并正与丹麦同行共同进行猪基因研究外,对人类基因排序作出了主要贡献。除2002年12月上旬宣布已成功完成水稻基因详图的绘制工作,该所也参与了由5个国家于2002年10月共同发起的国际HapMap项目,旨在对人类基:因的多样化及其对人类疾病的影响进行大规模测序以强化人类基因项目的研究。
类似的例子还有在英美受训归来的工程和分子生物学家陈景(音),他现在正领导着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生物芯片技术所(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Beijing Biochip Technology)。陈博士是中国最富有企业家头脑的学者之一,他已经把该中心的一些技术转让给了中国和美国的一些工厂。现在他有两个诊断芯片,一个用于传染病诊断,另一个用于人体组织移植。
位于上海的中国国家人类基因组中心是另一个热点。他们的研究正集中在引发某些疾病的基因上,特别是肝癌这一类危害中国人健康的疾病。
中国正开始使用某些生物技术以增强传统中药的疗效。在香港,生物工程研究所把分子从传统中药中筛选出来以观察其对神经性退化疾病患者的作用,这是一种在西药研究中常用的技术。上海传统中药发明中心已经和美国一家生物工程公司PhytoCeutica进行合作,创建一个拥有9000种传统中草药和15万个处方的数据库。
中国正在一些中心内筹划进行干细胞的研究。绝大多数的中国干细胞专家把成年人的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五、六个干细胞库。然而,有一些专家正致力于胚胎干细胞的研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沈惠珍(音)就是这些专家中的一员,她试图将人类皮肤细胞的细胞核移植到兔子的卵细胞中去从而培育出干细胞。
沈博士的实验完全是理论性的,她想更好地了解细胞重新编序的初期状态,这项实验所需要的数千个卵细胞难以从人类那儿获得。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作了十年之后,她决定回到中国,因为越来越多的限制使一系列的研究难以进行下去。中国学者回国寻求在西方难以得到的学术自由,这确实是令人感兴趣的。
对所有这些研究工作来说,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受到制约的因素之一是经费问题。生物技术花费巨大:发展所需时间长以及成果的不确定性意味着要花费很多的钱才能搞成一项产品。在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生物技术是由政府资助的,尽管也有少量的私人资本开始慢慢地渗入其中。
总体上说,像沈博士这样的生物技术专家宁可需要私人资本,而不太情愿接受伴随公共资金而来的附带条件。但至今为止,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远不如他们的国外同行那样敏感。上海基因中心主任赵国平(音)曾见过不少百万富翁敲上门来,但当他们了解了生物技术所具有的风险后便扭头就走,而来自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投资者却决定冒险一试。然而,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风险资本集团在没有看到有可靠的回报之前是不会贸然投资的,最好的办法或是通过股票市场筹资开办一家咨询公司或是将此项目卖给一家大公司。
第二个问题是经营管理问题。犹如欧洲生物技术的早期发展那样,中国这一新兴产业缺乏的是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商业意识的人才。此外,知识产权保护也还不够充分,虽然2001年中国加强了对药品和其他生物产品的专利法的宣传和执法力度,但由于执法机制不健全,人们要想取得专利还是非常艰难。
最后一个问题是规章制度。中国在诸如堕胎和器官捐献这样的生命伦理禁区的管理尚不健全,使不少西方人在听到中国又在开始从事基因工程或高技术再生工程时感到担心。然而,德国波鸿大学的生物学家奥利 · 多林(OleDoering)却争辩说,中国进行生物工程研究的同时也引进了现代生物伦理规范。中国政府早在1998年就明确宣布禁止人类的克隆,而美国正在等待通过国家立法;同样,中国的人类基因组项目在样本采集和知情同意方面也受到严格的条文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近唯一进入生物伦理禁区的不是别人,正是由哈佛来华访问的一群基因采集者。
农业革命
然而,一说到转基因水稻的规则,事情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杜索成(音)是一位在北京附近村子里种棉粮养鸭子的农民,他坐在新近建成的水泥屋子里指着那台新买的二手卡车说,他对于那0.3公顷的一小块Bt棉田带来的额外收入非常高兴。他所培育的Bt棉能产生一种细菌中常见的蛋白质,对中国主要农业害虫之一的棉铃虫来说,这是一种致死物。虽然它的成本比一般的棉籽要高,但杜先生认为,从降低杀虫成本和提高产量的角度看,还是物有所值。他还打算在明年扩大他的Bt棉田,他的妻子早就希望他这样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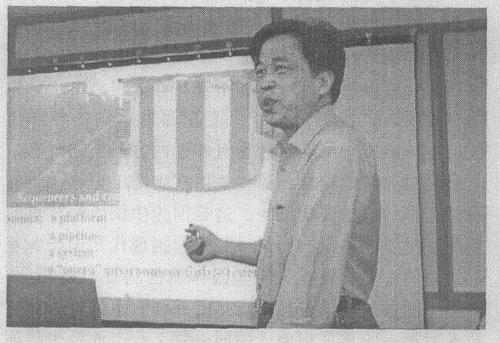
图为杨焕明教授
杜先生的经验在中国得以推广,据中科院和中国农科院的农业政策专家黄继昆(音)和王庆方(音)的统计,去年大约有500万中国农民在200万公顷的土地上种植Bt棉。黄博士和他在美国的同事戴维斯以及拉特格斯大学的卡尔 · 普雷(Carl Pray)和加州大学的斯科特 · 罗泽尔(Scott Rozelle)所作的研究显示,种植Bt棉的农民收入比种植常规作物的农民收入差不多每公顷要多500美元,而使用的杀虫剂要少80%。罗泽尔博士认为,这一事实很有力地反驳了转基因作物没有给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带来什么的观点。
Bt棉是被准予在中国进行商业性培育的四种作物之一,其他三种分别是晚熟西红柿、抗菌甜椒和变色矮牵牛花。此外还有多种转基因动物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60种转基因植物,包括抗病毒小麦、抗飞蛾杨树和一种能产生乙肝疫苗的高技术西红柿。
2000年中国政府在生物工程植物的研究上投入了3.22亿元人民币,极有力地支持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农业科学计划中的一个项目。位于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是中国的植物生物技术中心之一,在那儿,张启发(音)和他的小组专门对中国主要商品粮的水稻进行研究。2002年11月,中央政府宣布,除了其他政府渠道和私营发展商提供的6500万元外,中央政府向该大学提供1500万元设立一个培育新的转基因作物的研究中心。
然而,中国政府给出了一些模糊的信号。张博士的Bt水稻已经通过现场试验产生积极效果。隶属于政府的国家CM生物安全委员会也早已批准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进行这种水稻的试验。但是两年过去了,该委员会却不同意出售这种水稻。张博士不是等待开故绿灯的唯一的一位专家,尽管自1999年以来一些Bt棉的新品种已经该委员会批准,但是没有一个新的转基因作物在市场上销售。就连张博士也感到迷惑不解,为什么政府舍得花本钱去搞研究,而且还进行环境试验以求进一步改良,却不同意将此成果推向市场呢?
2001年宣布的官方理由是,国家对转基因作物的食物归类、环境试验、商业销售和进出口有严格的新规定。新的进口规定包括要求进行现场试验和提供食品安全评估。一些科学家认为,考虑到中国下一代转基因作物包括诸如水稻这样一类商品粮将被世界上数十亿人所食用,而其安全性又掌握在中国的手中,采取更为谨慎的做法是正当的。
而其他人就不怎么客气了。如美国的Monsanto公司和Cargill公司在2002年初得知,要求它们三个月后按新规定办后就大光其火。结果,美国几乎停止了所有对中国的大豆出口,这相当于中国大豆年消耗量2500万吨的一半。因为大豆的库存量在6月份下降到了谷底而使价格上涨,国内的大豆生产者便大发其财。
虽然中央政府正在处理进口商提出的新的准入申请,这一短缺状况至少要到2003年9月后才能获得进口大豆而缓解。实际上,看来贸易和安全一样都可以检测中国在转基因作物上的新立场。中国作为WTO成员国向世界开放给国内毫无竞争力的生产商造成了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中国试图利用它的生物规定去回击来自美国的竞争不必大惊小怪。
但是,真正的问题也许是出口而不是进口。中国农业大学校长陈章亮(音)将此归咎于欧洲人惧怕转基因食品。中国已经尝到了基因歧视的滋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利用一种转基因作物——抗菌西红柿来赚钱,但在遭到美国一些烟草公司反对后很快就洗手不干了。最近,中国的出口商又遇到了麻烦,欧洲人拒不接受含有美国转基因大豆成分的酱油,并对从蜂蜜到蘑菇在内的所有食品的基因纯洁度提出质疑。
怀疑的种子
尽管大豆事件受到媒体的极大关注,但是在中国关于转基因食品的报道调门比英美都低。2001年一个反对转基因作物的绿色和平组织将一份月报寄送给大陆的600名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现在该组织已经将其在香港的总部搬迁到了北京,这一事实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与此同时,绿色和平组织试图拓宽公众讨论的范围——2003年初计划在广州和_上海开办公众教育课程。
黄继昆博士最近对20个城市的1000位消费者作过一次随机调查,初步结果显示公众的知情状况相当差,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从未听说过什么转基因食品。当然,一些虔诚的道教徒和佛教徒出于宗教考虑强烈反对转基因作物的培育,特别是当这些基因不是来自植物本身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然而,从总体上说,从黄博士的调查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被调查者可以接受转基因作物,五分之二的人甚至欢迎转基因作物。但是差不多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对此却不置可否,他们很可能成为绿色和平组织撒播怀疑种子的沃土。
生物技术反对派面临的是一场持久战。中国肯定不会像欧洲那样中止对转基因作物的试验,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可能放弃对干细胞的研究,不过,上述这些问题,或者说那么些值得注意的事情,看来有可能成为今后中国生物技术大发展的羁绊。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2002年12月12日]